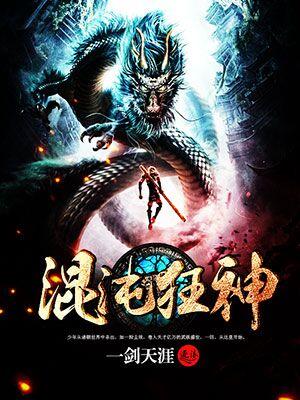爱上中文>火上眉梢 > 第四章(第3页)
第四章(第3页)
李清赏把批改的学生大字往怀里一颠,趁机挣开了蒲典的挽胳膊,她有些不大习惯这般亲密地和别人肢体接触。
蒲典素爱凑热闹,难得死水无波的生活里见到位陌生人,八卦道:“你房东说话软糯糯,蛮可爱呢。”
李清赏微笑未语,心说那是你没见过君主翻脸,比翻书快。
“夫子好。”
有路过学生给二人问好,打断蒲典原本的话题,她应了学生,改口问李清赏道:“你身体彻底好了罢?”
“只是不慎吃冷风,已经痊愈,不会传给人。”
李清赏不好意思让人知是痛经请假一日,正好赶上旬休又休息一日,那股劲过去后便不再疼。
“没事就好,”
说话间走到夫子们上差的差房,蒲典推门进:“你不在这几日戊班曾芹也没来,听说她爹又闹腾不让她念书,没娘孩子实在可怜。”
戊班曾芹六岁,还没李昊大,也是没娘孩子,她爹嫌曾芹上课耽误给他做饭洗衣,三不五时闹一番不让曾芹上学,回回都是学庠山长童山长去沟通,每次童山长皆是一再退步,曾芹父亲才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答应让女儿回学庠上课。
其实曾芹不上学庠又如何呢,对谁都造成不了损失,不过是童山长不想放弃孩子。
闹到现在,童山长不仅自掏腰包管了曾芹午饭,还被迫管了曾芹他爹午饭,这回曾父再闹,不知又是在打甚么主意。
对于蒲典的八卦,李清赏笑笑没应声,天下可怜人数不胜数,轮不到她去同情别人。
学庠上课一忙半日。
至中午,下课,李清赏讲一上午话嗓疼,回差房倒热水喝,被从山长室跑过来的蒲典慌张惊急推着进差房。
“咋了?”
李清赏倒着水问。
蒲典关紧房门,又趴窗户后透过缝隙往山长室方向看,后怕道:“真是有不要脸的人,曾芹她爹来了,在山长室和山长提条件,”
说着转过头来看李清赏,尾音仍旧在发颤,“你知他这回要甚么?”
李清赏倒了热水靠在条桌前慢慢喝:“学费是朝廷免的,束脩他家也不用拿,童山长也管了他们吃饭,他还能有啥要求,总不能想要住学庠罢,我们这几间破屋子他看得上?”
山长那小室窗户还漏风呢。
“不,”
蒲典用力干咽一下,放低的话语字字不安,“我去给山长送月报书,听见曾芹父亲说曾芹没娘,提要求让山长从学庠女夫子里给他找个媳妇,我进去后他看了我一眼,吓得我拔腿就跑,亲娘哩,那种人实在太可怕!”
“啊?!”
这种要求简直突破人的认知底限,李清赏两手握住水杯:“山长肯定不会答应。”
“当然了!”
蒲典平复着依旧不安的呼吸,过来靠到放藤水壶的条桌前紧挨着李清赏,“曾芹爹看我的眼神比坊楼下那些闲汉还让人恶心,以后咱进出真要小心了,听说以前就有下去府县支援的学庠女夫子,被当地人抢走硬娶作媳妇,若实在不行我就让我爹接送我一阵子,真是吓人。”
见李清赏沉默,蒲典想起她是孤身在此的外乡人,建议道:“不然你让你那个房东接送你一阵子?”
李清赏失笑:“她也是女子呀。”
“你房东看起来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
蒲典道:“好歹她站那里比曾芹爹高大,能吓唬住坏人就是管用的!”
“我回去和她商量,”
李清赏喝了水润嗓子,仿佛并不在意这件事,甜甜笑着,眼睛弯成一条缝,唇红齿白:“我们去吃饭罢,下午还是满满课,得先吃饱。”
蒲典拉着李清赏胳膊一起往外去,嘴里不停说话:“赶紧去给那夫子和列夫子也说一声,让她们小心些,实在太可怕。”
。
汴梁城内数县辖,住民百万余,吞吐往来又是数十万巨,地大人多,管理起来各处有各处规矩,连学庠也是。
李昊所在的前街学庠申正下学,李清赏那边申末结束,柴睢上午忙自己的事,下午踩着点先来接李昊,接孩子下学,这于太上而言其实是蛮新鲜的经历。
铜钟声响彻学庠内外,幅巾青袍的大小学生们呼朋引伴下学,李昊甩着他姑姑亲手缝制的装书布包一蹦三跳冲出来。
“姑父!”
他比柴睢更先找到对方,兴高采烈出现在柴睢面前,为柴睢的守约而高兴。
只见他把布包带子反挂在脖上,头上幅巾歪着,小胸脯挺老高:“我已经约了段星驰,他答应下学后在那边卖狮子糖的巷口等我。”
“做的好,”
柴睢赞他,越过街上乌泱人众眺目搜寻卖狮子糖的巷子口,“我们何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