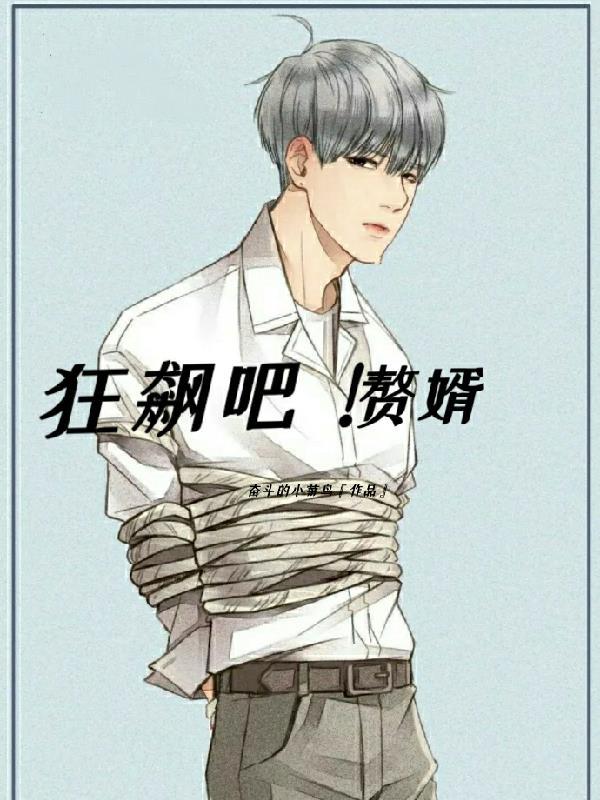爱上中文>千岁词简介 > 第101章 惊梦(第1页)
第101章 惊梦(第1页)
昭歌不夜城,九宸殿。
龙床之上层层明黄垂幔下,一双指节因过度用力微微痉挛的掌心湿淋淋的,少年天子额间满是汗水。
他在做梦。
噩梦。
梦境里少女瑰丽出尘的脸时隐时现,她浅金月白的神袍上不知何时溅满了淋漓鲜血。
有紫褐色的,也有鲜红色的——颜色较深的血迹是中毒颇深、渗入肺腑的毒血郁结之色,鲜艳如火的则是强行冲破被毒封锁的心脉时、生生震断全身经脉内腹的残败之色。
梦中人唇角开阖,似乎本是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但不知为何,最终却始终一言未。
而梦里的天子心中却突然涌现出一股无言的、不可说的苍凉与惊慌!
他仓皇上前一步,似乎想捉住梦中人喋血的袖摆。
“不要走!你信朕,朕、朕我不是想要你的命,你别走!”
但下一刻,天子怔忪的看着自己空空的掌心,原来,到头来他还是什么也抓不住,一如他拼命追赶、却永远徒劳无功的一生——
所愿皆不得,一切皆成空。
“你为何不说话?”
他喃喃的看着始终与他保持一段若即若离距离的少女。
“即便是入我梦中,你都不屑于再与我多说只言片语吗?”
“我只是,我只是想要你留下啊!”
他突兀的哽咽失声,“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分明是你固执,是你冥顽不灵,是你放不下神女的地位和尊崇!是你!背弃了朕啊!”
梦里的天子情绪激动,几乎语无伦次,甚至时而称呼自己为“朕”
,时而称呼自己为“我”
。
他的心,早就乱了。
但是梦中的少女却始终眼带悲悯的看着他,无声无息,好像一缕幽魂,好像早已不是这个世间之人。
少年天子的心更慌了,他突然扯开衣领,竭力掏出贴身挂在颈项上的玉葫芦。
“解、解药!我早就准备好了解药,我绝不会害你的!
我本就打算只在宫中关上你一阵子让你收收心,待你过了十八岁愿意脱下神袍了,便放你出昭华殿的。你看!”
少女忽然笑了。
眼底似有不解,似有失望,似有释然,似有放下。她的笑容既淡,又复杂,以至于少年天子一时看不透彻分明。
少女周身散着淡淡的莹白金光,但那光芒却越来越淡,同样变淡的还有她本就模糊缥缈的轮廓侧影。
她突然轻轻道:“言儿,时候到了,我该走了。”
“不!不要走!”
但梦中的少女最后看了他一眼,然后终于还是转过身去,只留给他一个浅到几近于无的背影。
她永远都有自己的主意,仿佛从来不会屈从于任何人的命令。
她只会遵循自己的心,不论是生、亦或是死。
就连她的生死,都要自己掌控左右。
“——阿姐!”
下一刻,龙塌之上,靖帝符景言喉间挤出一丝濒死般的沉重喘息声,然后整个人猛地惊坐而起!
他终于挣脱噩梦,醒了过来。
“陛下!”
昭歌城章印大太监袁艾在听到动静的第一时间就立刻醒了盹,他顾不得烫手、连忙从一旁一直喂着火的暖炉上端起一个药盏,然后膝行几步上前靠近龙塌,恭恭敬敬的双手将药盏举过头顶,小声安抚着天子:……
昭歌城章印大太监袁艾在听到动静的第一时间就立刻醒了盹,他顾不得烫手、连忙从一旁一直喂着火的暖炉上端起一个药盏,然后膝行几步上前靠近龙塌,恭恭敬敬的双手将药盏举过头顶,小声安抚着天子:
“陛下,可是又做噩梦了?这是刘院使上次开的静心聚气的汤药,说是陛下若再被梦魇住,便喝上一碗,心神定会舒坦许多。”
十九岁的少年天子、如今已是南朝天宸靖帝的符景言,抬起手撑住自己胀痛的额角,除了喘息,再无其他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