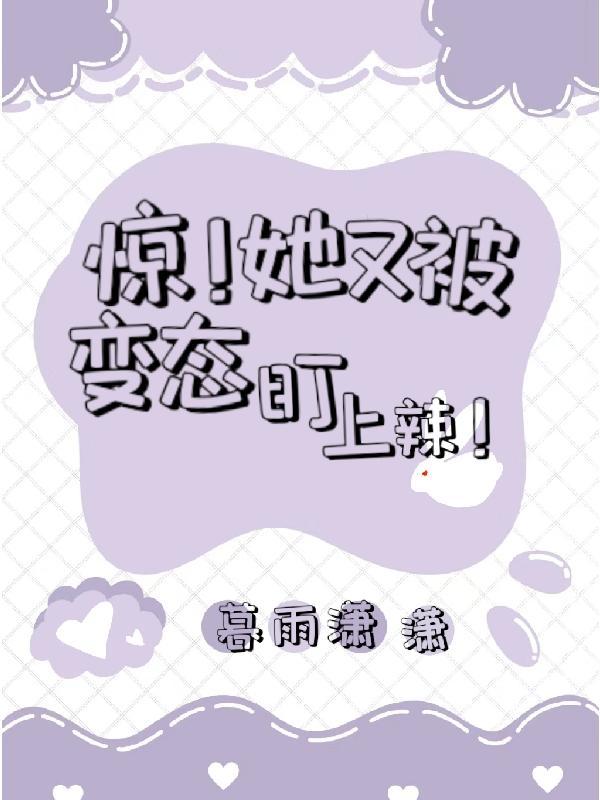爱上中文>月夕花晨解释和意思 > 第8章 自由落体(第3页)
第8章 自由落体(第3页)
我根本就没明白吴晓诚说的是什么,但是我又耻于问他,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没有见识。
原哥忽然探身对我说:“你还记得郑三牛吗?”
我说:“记得,头几天还看见他了呢,跟两个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原哥轻蔑地“哼”
了一声,说:“他死了。”
我吃了一惊,忙问:“他怎么死的?”
“头些日子边上那楼着火了,你知道吗?”
原哥伸手指了指之前着火的那栋楼。
我说:“我知道,那天我一同学住我们家了,我们还听见爆炸声了呢……啊?那不会就是郑三牛家吧?”
原哥和吴晓诚大笑起来,他们甚至笑得喘不过气。过了约莫半分钟,原哥涨红着脸说:“你们听见的那个哪儿他妈是爆炸声儿啊,那是郑三牛跳楼摔在地上的声儿。”
我又是一惊。原哥给我讲了讲他所知道的事情的始末。
郑三牛家拆迁之后,分了四套房,全都在他的父亲的名下,他的母亲早就被他的父亲送到了精神病院。郑三牛家有钱了,但是他的脑子依然不灵光,后来他误入歧途,开始赌博(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就是原哥带他进的圈子,原哥一定从中捞取了某些好处),一年多的光景便把家里的两套房子都给造没了(也是原哥帮他找的“中介”
)。上次我们在自助餐厅相遇的时候,是郑三牛去借高息贷款(还是原哥给他找的人,原哥说的是高息,实际上就是高利贷,九进十三出)。我在初六那天遇到郑三牛的时候见到的两个陌生人,实际上就是高息贷款的暴力催收人员。他们从上午就在郑三牛家敲敲打打,郑三牛的父亲似乎早已经熟悉了这个场面,熟视无睹。到了晚上,由于暴力催收人员侮辱郑三牛的手段过于低俗,郑三牛的爸爸终于勃然大怒了,他和催收人员推搡起来。试想,一个五十余岁且被烟酒掏空身体的中老年人与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动起手来,形势孰优孰劣,一目了然。郑三牛吓得嚎啕大哭,郑三牛的爸爸倒地不起,催收人员更加暴力,打砸起来毫不留情。郑三牛终于也愤怒了,他终于挺拔了一次,而这一次,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且是最后一次挺拔。郑三牛把他爸的六十二度塑料桶装二锅头泼到了催收人员身上,并且用打火机点燃了他们。二锅头不是儿时玩过的粘手,它无法准确地仅落在催收人员身上,我是说,这些六十二度的二锅头也洒在了他家的床单上,窗帘上,而这些易燃的材料,随着他点燃的zipper打火机燃烧起来。两个催收人员见郑三牛如同疯牛,也有些害怕,他们迅扑灭了身上的火苗,夺门而出。郑三牛应该是绝望了,他打开窗户,没再看他爹一眼,而是平静地从十楼一跃而下,出了他这辈子所能出的最大的声音。
括号里的话,都不是原哥给我讲的,而是我在之后走进原哥和吴晓诚一步一步设好的圈套,自己经历了一遍之后,悟出来的。
我当时应该想到,如果不是这些搞高息贷款的人给原哥讲了那个房间中的事情,他是如何知道如此详细的呢。
听完原哥的讲述,让我大为感叹:“唉,郑三牛也是,本身脑子就不好使,非得去赌,丫也是活该。”
原哥和吴晓诚又对视一眼。吴晓诚说:“嗐,咱们哥儿仨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聊个死人干什么……哎,江乐,你要是有钱的话,可以放放高息贷款啊,这个来钱也挺快的,你要是放心我的话,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去弄。”
说罢,他冲我扬了扬眉毛。
我摇摇头,客气地笑笑:“算了吧,我可不敢沾这些玩意儿。”
吴晓诚又点燃一支我的烟,说:“你丫从小就胆儿小,都是让你爸妈给管的。”
原哥说:“哎,晓诚,你别这么说江乐,他跟咱们不一样……江乐,你别搭理丫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吧。”
吴晓诚说:“江乐,不是哥们儿说你,你就跟笼子里的鸟儿一样,现在把你的笼子打开了,你也不会飞出来。”
吴晓诚的话让我很不高兴,我想告诉他,我他妈不是笼中鸟,虽然我不是什么雄鹰,但我绝对不是什么狗屁笼中鸟。
原哥应该是看出我的脸色不对,赶紧打圆场:“得了得了,都别废话了,一会儿等你嫂子做完饭,咱们好好喝一顿吧。”
少时,原嫂把一道道菜肴端到餐桌上,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招呼我们吃饭。
饭桌上,吴晓诚频频向我敬酒,再次说着他应该让他妈把他妹妹嫁给我之类的话。我忘了他刚刚对我的“羞辱”
,听到他说他想把妹妹给我的话之后,我感到很受用,于是,在我酒精上头之后,询问了他妹妹的近况。
吴晓诚告诉我,他的妹妹现在在一家公司当行政,是在结婚之后,她的公公给她找的工作。吴晓夕应该和我一样,也是大专毕业,与我不同的是,她一毕业就结婚了,然后参加了工作,而我却还像个孩子一样,整日在家里玩游戏,偷窥对面楼里的姑娘。
我问吴晓诚:“吴晓夕结婚之后还幸福吗?”
吴晓诚还没说话,原哥却在听到我话后,被口中的酒呛到,一边笑一边大声咳嗽起来,原嫂赶紧抽了几张纸给他擦嘴。原哥涨红着脸,一边擦嘴一边说着不好意思。
吴晓诚也笑了,他说:“我妹妹两口子的事儿,我怎么问的出口……江乐,你丫他妈的想什么呢?”
我不解:“我没想什么呀,我就是想问问吴晓夕现在过得怎么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