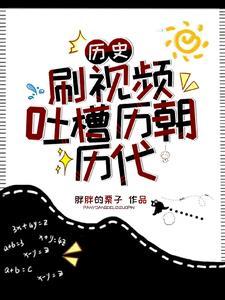爱上中文>清穿葬礼王爷很快乐百度 > 出游小少年(第5页)
出游小少年(第5页)
一个州县里的黑色地带,莫过于这群牢犯了。
根据他们的言语中,似乎这里面就有五人是真的冤枉的。起初只是平头百姓,但都因为部分原因与人争执,或者碍了眼,就像弘昼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丢了进来。
就等着统一落下罪名,人齐之后被押送远方。
这种剧情听着像是一百零八个好汉,但基于自己也是相差无几的情况,弘昼心里不免戚戚。他看个地皮能抄家,出来打个架就可能没命?这样的时代背景,真的投胎是件技术活!
但无论如何,一个小地方就有这么多的垃圾小事,着实是让他惊住了。
从某方面而言,弘昼曾经也
觉得胤禛的方式过于绝对,应该徐徐渐进之后再铁律刀下。可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合适的机会?
大概是没有。
弘昼没有说话,他们就鼓着劲儿,将所有知道的坏事托盘而出。
或多或少也有些帮助,弘昼和旁边的阿林保都静静的听着,这一夜也几乎没有歇息好。
直到天未亮要交接班时,弘昼起身将昨日的衣衫穿上,再由阿林保给他扯乱了发型着装,显得几分落魄样子之后回到自己的牢房。
晨起送来的饭食很糟糕,弘昼看了一眼,那张饼像是馊了一样,他没打算忆苦思甜的去摸。
昨日的衙役换班上来,走到牢房前打开锁道,“县令大人宣见。”
弘昼回首,努力的从墙头小窗看一下光色,“好。”
堂上一如记忆中的模样,县令坐在高堂之上,身边站着个主簿,而他其后坐着的是刘石箜和陈德铭。弘昼上去之后,堂上站立两侧的衙役们,拿着水火棍齐齐喊道,“威~武~”
惊堂木在公案上敲响,官服礼戴的县令一本正经道,“台下是何罪犯?”
“叶良辰!”
“大胆!还不跪下!”
主簿连忙喝声,他眉眼不动,就有衙役要上门来强令让他跪下。
弘昼站得笔直,昂着下巴,“在我的讼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讼师?
怕是失心疯了?
刘石箜大老爷似的坐在旁边,闻言更是嘲讽一笑,“公堂之上不懂规矩,罪加一等!”
“你算
什么垃圾?公堂规矩还由你做主?”
“放肆!”
县令低声一喝,“尔无辜殴打知州之子,本县令将你押送牢房静思一夜,你不仅不懂反思悔过,反而越发无状!”
“你管那叫静思?你确定不是虐待?”
“放肆!”
“什么放肆!这是实话实说!你身为父母官,只听知州之子的一面之词就定夺案情,话都不让我说两句关押了一天,可见你们就是沆瀣一气的土耗子!”
“你!”
“我什么?你们就是官官相护!纨绔子弟,连只鸡都要强取豪夺!真是笑死人了!”
弘昼几乎是指着陈德铭说的这话,这让场上人都顺势看了一眼。有些事情彼此明白,唯有刘石箜神色不满,毕竟抓人的由头是在他身上。
“来人!将这个不懂规矩的罪犯压下打十大板,日后再审!”
县令无法再在这里听这些拉扯无用的话,基于对方的身量较小,只打得他皮开肉绽吃点苦头就好。想来再晾两天,他就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静思了!
公堂上有人笑出了声,弘昼看着走近的衙役们,他们身上的牌子写着公堂二字。
即为重申和告诫,意思这是堂堂正正公事公办的场合。
弘昼呵笑一声,“所以说你们是承认了?”
自然是没有人回答他的,相反衙役们伸出手来,眼看就要将他拿下。
弘昼站在堂上,气定神闲拿出身上揣着的防狼神器伸出去——
衙役们像犯了羊癫疯一样颤抖
。
弘昼在惊呼中潇洒的退一步,“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