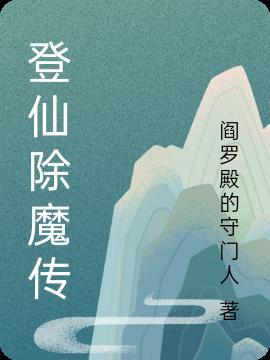爱上中文>双笙烟花易冷 > 第8页(第1页)
第8页(第1页)
家里却一如既往的弥漫着阴沉之气。伙计豆芽的耳朵被淑苇爸爸打聋了。
豆芽在迎接解放军进城这件事上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几乎天天往大街上跑,挤得鞋都掉了,成天嘴里哼着歌,没过两天便顶着趣青的头皮,在院子里大声地说,是解放军给剃的头,不要钱的。江裕谷阴着脸看着他,小伙计的快活在他的眼里显出点猖狂来,这叫他极不舒服。
这些天米价被哄抬起来,有些米店的老板开始偷着往大米里掺些碎谷子与砂子,很是赚了些钱。江裕谷看着不忿又眼热,便也开始往米里掺杂物,也就是那么巧,正被豆芽看见了,豆芽立时就叫了起来,说是要到解放军那里去检举他,江裕谷一个巴掌就甩了过去,这巴掌打得太狠,豆芽一个跟头就栽到地上,江裕谷也怕起来,叫人送豆芽去医院,说是耳膜打破了,等好了之后,豆芽的左耳就不大灵光了,因为听不清,他不仅斜视,更加添了歪着脑袋的毛病。入夏的一天,豆芽终于跑了。
也正是这个夏天,江裕谷的一个老朋友,也开着米店的,叫解放军给抓了,事情就坏在他往米里掺东西上,后来又听说哄抬米价也有他的份儿,没多久便给枪毙了。江裕谷吓破了胆子,从此倒老实做起生意来。
日子过得随顺起来,这一年的冬天,江裕谷娶了东牌楼从良的妓女云仙进门。
那天天特别冷,淑真与淑苇袖着手,站在小院门口,看着云仙穿了一件缎子的新棉袄,水红色,掐腰,紫红滚边,襟前塞了一条粉色的手绢,随着她的步子的起伏轻柔地扑打着,瞧着她这一付派头,打鼻子里用力地哼了一声。
云仙一摇一摆走到院子中央的时候,被一块松动了的青石绊了个趔趄,淑真响亮地笑了一声。
云仙却只当是没有听见,回头挑了细长的眉向身后的江裕谷抱怨道:“快找个人来收拾一下这砖头。”
说着扯了手绢在鼻翼处轻轻扑了一扑,目光凉凉地扫过姐妹二人。
继母
江裕谷的第二次婚姻来得悄然突兀而迅速。
淑苇的姐姐十七岁的淑真对后母的到来表达了无比地恨意。她云仙来的头一个晚上,饭桌上,她便以一张冷脸相向,她端正明媚的眉眼绷得紧紧的,更叫人想不到的是,她穿了一件母亲留下的旧淡蓝通花麻纱旗袍,满身樟脑的气息,侧了身好正面对着云仙,仿佛母亲的魂灵无声地归来,附着在她年青的身体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对狗男女,满目苍凉,不胜前世的万般感概。
江裕谷阴阴地看着大女儿,好歹没有发火,云仙则是一片悠然地捡了张妈的拿手好菜无锡糖排骨慢慢地啃。她十二岁入东牌楼,什么没有见过,岂会被一个小丫头虚张声势的下马威给吓住。
她是不得不嫁的。
再迟一步她便要被抓去做工改造了。云仙一辈子靠男人吃饭,养得细皮嫩肉,她如何能去手套厂一天到晚织上七八个小时的手套?或是去染料厂弄得满手五颜六色没得恶心?
云仙想,她还算是有运气的,急着要从良时便遇上了江裕谷,手里有几个钱,更重要的是,倒不是肥头大耳,面目可憎或是七老八十的,象她的一个姐妹,早些天便急急地嫁了一个快六十的老邦子,一开口那味道冲得人一个跟头。
云仙丢下饭碗,闲闲的扯了手绢抹抹嘴角,抬眼看到她左手边江裕谷的另一个女儿,那女孩子快捷地垂下眼去,额前的流海披下来,挡住了她的眉眼。
云仙灵敏的意识到这是一个温婉的丫头,不似她姐姐咄咄逼人,不禁笑了一笑。
对淑苇而言,随后母而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后母祖籍上海,总是一付南京是乡下小地方的派头。她爱吃零食,穿掐腰裹身高开叉的旗袍和玻璃丝袜,每日打扮得齐整了出门一趟,回来闲闲地坐着嗑瓜子,淑苇有一天无意间走到父亲的房门口,那正是晚间,从半掩的门里,她看见云仙以一种极其诱惑的姿态将那玻璃丝袜剥葱似脱下来,然后她竟然把那雪白的脚丫伸至站在一旁的父亲的脸旁,用脚背轻轻踢着父亲的脸颊。
淑苇回身迅速地轻得像只猫似地飞跑回自己屋子,将被子扯开盖到自己头脸上,流了一脸的泪。
这一个晚上,她梦见了那个一面之缘的年青身影,细长,高挑。她梦见自己站在他的面前,低着头,看不见他的样子,可是却觉得想跟他说出心底里无限的委屈。
天亮后醒来的淑苇为自己奇怪的梦境发了很长时间的愣,那个时候她不会想到,这个梦里的人会那样长久地温存地留在她心里,一直到她老死。
在淑苇梦里出现的沈佑书这一年初中毕了业。
他打算考晓庄师范。师范不要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费发放,母亲就可以不用那样辛苦,而且他还可以留在母亲身边,南京是母亲的老家,他不想将来母亲年纪大了还要跟他到异乡去。
六月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晓庄师范。在他的行李里装进了那个小铁糖盒子。
这一年过年的时候,江家又出了件大事。
年前,淑苇姐妹的后母竟然叫了裁缝来家,给自己做了两身新衣,并且打算给姐妹俩也各作了一套。
她叫了姐妹俩去量尺寸,说,这买的可是红霞布店新近的上海好料子,别叫人家说我这个做后娘的薄待了你们。
淑真倔倔地站着不动,不肯上前半步,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毒毒地盯着云仙,淑苇看姐姐的样子,也不敢上前去。
云仙却好像没有看见淑真,只上前拉了淑苇的手,扯了布料盖在她胸前,看那颜色衬不衬,又叫裁缝来量尽寸,淑苇僵僵地站着,由得裁缝摆布,一双眼只怯怯地望着姐姐。
云仙闲闲地说:“解放了,人都不要穿旗袍了。其实旗袍有什么不好?多么抬人,再丑的丫头,穿了旗袍也总有两分姿色。那一年我去上海,在和平饭店吃西餐,看到过胡蝶,穿了件淡绿色的湖绉旗袍,从前襟到下摆一路绣了银色的蝴蝶,那才是漂亮人物。不要以为自己略微周正些眼睛就长到额角去,你披了麻袋片子走出去试试,哪个男人多看你一眼?”
淑真突地冷声冷气地说:“贱人才天天想着要男人看。”
云仙刷地抬起眼,眉目间的颜色一下子深浓起来,有一种剑拔弩张的尖税感。
结果这一年的年夜饭,淑真依然穿着母样的旧衣服上桌,淑苇穿的则是新制的一套衣服。她是临上桌前瞒着姐姐换上的,她本能地,意料到饭桌上会是如何地针尖麦芒,暗自希望自己的这一做法可以缓和一点家里紧张的气氛。
可是淑苇却把自己的姐姐给得罪了,姐姐开始不大搭理她,说她没有骨气。淑苇变得愈加地沉默。她偷偷地把记忆中的那个人的背景画成一副画,只得一个背影,在一片幽深长巷中。淑苇从小爱画,只是无人想到要请人来教她,年岁渐大,她慢慢地失了那一点天赋,画上的人与影都十分粗糙,比例别扭,但是对于淑苇来说,却是无比珍贵。她十五年的生命里,没有过一个好男人出现,便是这样一个虚幻的影像也实实在在地慰藉了她荒芜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