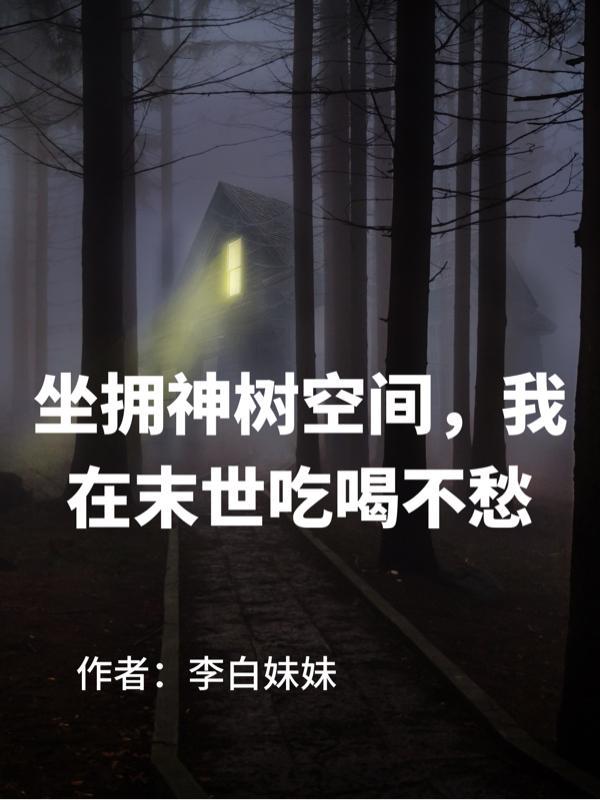爱上中文>玫瑰喷色用的是什么 > 第46章 他的热搜(第3页)
第46章 他的热搜(第3页)
……
檀和会馆,牌桌上。
自从祝曼上场后,时祺前半场赢的一堆筹码眼看就要输干净,其他两人也是一样,身前筹码寥寥无几。
反观某个之前说没兴趣的女人。
美眸轻敛,浑身透着懒倦,又带了股淡淡的不近人情,垒成堆的筹码都能打死人了。
以前她还会不屑地放放水,今天的她,大有一种不打死你们,我就不姓祝的狠。
“我说大小姐,你是受什么刺激了吗?”
时祺话刚落,祝曼漫不经心地扫了眼他,懒懒地勾了下唇:“怎么,祺少输不起了?”
时祺笑了声:“笑话,爷还有输不起的?”
“来来,继续来,今晚不输光谁都不能走。”
其他两人苦了张脸,打不下去了,讪讪地站起来,换了两人打。
中途换了好几拨人,只有时祺和祝曼两人坐如钟。
结束的时候,时祺眼神颇幽怨地扫了眼对面盆满钵满的女人。
还好,输得不算多。
也就最好地段的一套别墅和两辆心爱的跑车。
不多不多。
就是他爸知道大概得给他一电炮,再给他这个败家子关家里几个月不要出门。
祝曼回视着他,淡淡一笑:“少爷,客气了啊。”
话落,她款款起身离开。
留下时祺在原地郁闷:“丧心病狂。”
祝曼回了祝园。
凌晨两点多。
法式风的大卧室中,祝曼正睡得熟,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响了。
她没接。
铃声断了几秒后又再次响了起来。
祝曼被吵醒,没多温柔地拿过手机,看都没看地按下接听,语气很不好:“谁?”
男人先是低低笑了声,随即又淡淡开口,嗓音低醇又慵懒:
“这么久没见,祝总想我了吗?”
祝曼顿时气更不打一处来,冷冷抛下一个字:“滚。”
说罢,手机关机,扔了出去,落在地毯上,出闷闷的一声。
“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