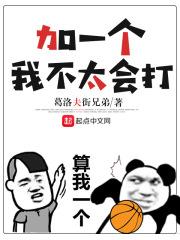爱上中文>被虫族抓住的小怂包免费阅读 > 第100章(第2页)
第100章(第2页)
算了吧。禅元自暴自弃地想,早知道洗澡就不摘除通讯设备了。这样还能通知伊泊和甲列,叫两人带上被困的军雌们,赶快逃离这辆雪地车,联系大部队。
一个人换十五个人,上级怎么说给自己颁一个“烈士”
头衔不过分吧。
就是小扑棱……小扑棱。禅元心中一痛,想起临走前被自己装在纸箱子里的小崽崽,笨拙叼着奶瓶迷迷糊糊要抱抱的样子,恨不得穿越回出前,抱着孩子亲上七八十口。
希望,提姆指挥官是个会带孩子的人。
寄生体依旧在喋喋不休讨好雄虫。他声音如雷,洪亮到门外匆匆赶到的伊泊听得一清二楚。军雌屏住呼吸,连退数米,最后在一个隐秘的制高点,寻找到藏身处,悄悄地架起了枪械。
队长果然遇到了麻烦。
他的瞄准镜对准了浴室里的二人。雄虫若有若无地朝这个方向看过来,惊得伊泊差点扣动扳机,整个人寒起来。
“阁下,那边有什么吗?”
寄生体大五全身心都在雄虫身上。浴室的热气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水汽反而叫整个空间比外面更寒冷。他脱下衣服,学着禅元登上车时的样子,想给恭俭良披衣服。
恭俭良丝毫不给脸面,一把挥开,“你说得都很没有意思。”
“抱歉。阁下。是我的错。是我嘴笨,全部说一些凌迟、五马分尸的老戏法。”
这点也是和禅元学得。
及时道歉,摆正态度,早点请求雄虫原谅。
寄生体大五善于学习,虽然是第一次跪舔雄虫,却因有前辈带路,次实践便早早体验到了跪舔的快感,一时间爽得难以自拔。偏偏雄虫脸色随着他的话,似有变化,叫寄生体心情大好,快马加鞭,舔上加舔,务必让恭俭良从身到心舒舒坦坦,开开心心送前任上路。
毕竟前任不上路,后来者哪里有位置啊。
他还指望学着前任,将浴室的事情重新做一遍。寄生体的身体可比雌虫强多了,寄生体大五自信能任由恭俭良糟蹋,无论是毒打还是□□,他都会放松身心去舔雄虫。
这都是恩赐,是恩赐啊。
他是寄生体,又不害怕死亡。大不了,濒死前换一具身体,继续开始。最底层不是还关着十五个远征军军雌吗?寄生体大五算盘打得啪啪响,已经开始预测自己寄生一次最多可以和雄虫做几次,每次要舔雄虫的哪里,才能雄虫爽到流淌出液体。
“阁下,我看您身上有一些脏。我来帮您擦一擦吧。”
寄生体大五继续学着禅元,他从口袋里掏出干净的毛巾,意图从脸开始帮恭俭良擦拭污垢。
他上前一步,骤然眼前一黑。
恭俭良手持铁锤,砸向寄生体大五面部,下一瞬间,手掌中小心捧着的爱心泡沫捏碎,攥成拳头狠狠捶打中寄生体腹部,从指间诈出二十厘米长的尖刺,将人捅个对穿。
“你是在学他吧。”
恭俭良轻声说道:“姿势学得很像,道歉也很及时呢。”
禅元也总是在他不开心的时候,光道歉,屡教不改,次次再犯。仗着恭俭良离不开他日常照顾的本事,端得就是一个有恃无恐。
恭俭良平日享受,心里又觉得难受。他清楚对禅元来说,这像是一种等价交换。他做错事情反而会让禅元开心拿捏住把柄,做得太错,禅元也只会气恼自己的晋升遇到了困扰。
这种想要又想要,恭俭良早就厌烦了。
他抽出铁刺,对准寄生体的胸口再一次戳进去,语气温柔,“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他吧。”
寄生体大五看着向腹部,这点伤害不算什么。可他一时间也不懂雄虫的心理,又舍不得对如此漂亮的脸下手,一个劲抛眼神给靠墙的禅元,想看看他在说什么。
禅元醒了。
他早醒了,半眯着的眼努力地睁开,望向自己呵护在手心足足一年的雄虫。
恭俭良手起刀落,他忽然抛弃抛弃铁锤,双手死死按住寄生体的脑袋,从禅元的角度看,就像是恭俭良用力地拥抱住寄生体€€€€他经常要禅元这么抱着,有时候是公主抱,有时候是面对面的抱,无论是什么方式,恭俭良都喜欢双手抱住禅元的脖子,按住他的脑袋。
他也会这么对待别人。
这个认知让禅元烧干净的心,吹来一阵风,洋洋洒洒一片干净。恭俭良对他没有半点用心就算了,事到如今,这个没有心的小玩意果然是谁有奶谁就是雌父,上门来者不拒。
别人命里什么情情爱爱,恭俭良缺得是个伺候他的人!
禅元越想越觉得自己亏条命不值得。他见恭俭良越好,越不想死€€€€凭什么?凭什么这种垃圾都能活着!我活不下来?我就是有点见不得人的嗜好,我又不是变态。我为什么活不下来。
他呓语着,自觉对恭俭良没有半分感情,咬牙切齿,“雄主。”
“禅元!”
恭俭良开心地拧过寄生体的脑袋。他度极快,手腕和手臂在一瞬间力,还不等寄生体大五反应过来,脑袋被转了一百八十度,对向后背的禅元。
“你放心,禅元。我不会让任何人用那么无趣的方式杀死你。”
恭俭良情感充沛,听上去像表演课深情的诗朗诵,“就算你后悔,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也不喜欢你。我们半斤八两,天生一对。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能代替你。”
他语序颠倒,词不达意。
无论是寄生体大五,还是雌君禅元,谁也听不懂恭俭良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