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文>相卫是什么意思 > 第99页(第1页)
第99页(第1页)
“我儿子,是要科考走仕途,不能有这么个父亲。你且带了他回去,早晚督促读书习字,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好官。”
梁祈看着儿子目光温柔下来,满是期冀。
“你叫他因此离你而去,自是不孝,不孝之人读书作甚!读了也是个不懂道理。”
梁夫人声嘶力竭,音调变得奇异,带着穿透力沙哑,以及绝望心碎气息。想要上前,却被跟来衙役拉住,挣扎间场面混乱。
“你是叫我死不瞑目!”
梁祈转过头,声音沙哑悲从心头起,红着眼睛面带悲怆地看着梁夫人,衫摆被山风吹得猎猎抖动,显出他瘦弱。
“相公!”
梁夫人急火攻心,高声哭喊便气息不足昏倒地。婉苏赶紧上前扶起她,又将梁祈儿子护怀里轻轻安慰。
小家伙如受惊小鹿,不明所以地看着前面父亲,想要投进他怀抱,却又觉得父亲此时面目有些陌生。
婉苏计上心头,轻轻推了梁祈儿子肩膀,小声道:“去将你爹爹拉回来。”
小小人儿受了鼓舞,撒欢跑向梁祈。本是一心寻死梁祈见儿子跑向自己,又急又气便迎着走了几步,抱起哭得跟个泪人幼子,心如刀绞。
梁祈看着自己夫人倒地昏厥,本已有些动摇,此时见幼子摇摇晃晃跑来,心一下子便软了下来。抱着幼子闭上眼睛挤出两行清泪,但仍不能原谅自己。
“既然自知罪孽深重,便堂堂正正受罚,未免牢狱之苦便选择跳崖,是大丈夫所为吗?那是懦夫所为!你也是饱读诗书,为官作宰这几年,难道不知圣人有言,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憨老爹已因此而去,却也死得其所,可你这一去便是将烂摊子都丢给了妻儿。那邝家得知此事怎能善罢甘休!你虽写了休书,但他们仍会拿了你妻儿撒气,这是你所想!”
婉苏见梁祈一根筋撑到底,只好用另一个角度来“劝说”
。
古阵暗暗叫好,见梁祈果真面有忧色,趁其不备便上前将其按住,两人滚作一团。古阵心头一松,只要人活着便有希望。梁夫人悠悠转醒,见梁祈已经来到自己身边,便死力抓着自家相公衣襟再不放手,只剩嘤嘤哭泣。
众人回到大兴县衙,昔日县太爷此时却成了阶下囚,因情况特殊,暂且先押到一处空房间,待上报此事后才能有所定夺。
或许是早有预感,冷临对王取到来并不吃惊,见其风尘仆仆赶来,便将事情前因后果讲明。
邝贵对于王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是此事将会对关碧儿产生什么样影响。前番关家有意悔婚于陆家之事,已惹了诸多风言风语,此番若是再有什么蹊跷事,恐怕众人唾液便足以将一个女孩子杀于无形了。
王取皱眉问道:“如此一来,邝贵应是那梁祈所杀?”
王取并不希望是这么个后果,虽说通过陆续而来消息,邝贵不是个可以托付终身之人,但他仍不想以这种方式叫关碧儿“脱离苦海”
。
“目前来看,有可能是。”
冷临回道。
“有可能是?这么说还有可能是旁人杀了邝贵?”
王取不明所以,不理解冷临咬文嚼字。
“下官意思是,关于此案,还没有个定数,因有些细节还找不到合理解释。”
冷临正色道。
“这人证物证,尸首也已找到,且梁祈供认不讳,还有何不明?”
王取奇道。
“邝贵已死,不假,但他第二日为何从青楼去了戏园子后,又返回客栈拿了金银细软离去,此处讲不通。那是他自己财物,为何悉数卷走!为何丫头下人一个都不带!是遇到何事!想必他这种人也不会有什么杀身之祸,即便遇到什么人威胁自己安全,也应是齐结了家下护着自己,绝非是那种敢于只身犯险之人。”
冷临说完,又对王取说:“为奇怪是,他会走那条路,沿着河边,人迹罕至不说,且是上山之路,莫非想躲进山林?是什么事叫他如此作为!这么个纨绔,怎好似江洋大盗一般。”
王取听了不觉一愣,幽幽道:“许是,遇到什么债主!”
“下官已查明,他并无赌债,便是前些日子常流连赌坊,月底了,家中也早替他还了。再说赌坊会叫他害怕到慌忙逃窜!连听到些许声音都要趴低匍匐而行,这绝无道理。下官也查了,他也未惹上什么权爵之人,况有梁远侯名头,一般小事也不至于叫邝贵吓破了胆,除非……”
冷临说着看向王取,富有深意说道:“王大人是叫下官如此结案,还是将这几点深究下去?”
王取自然晓得冷临意思,两人交往虽不多,但却彼此欣赏,便坦然道:“关家小姐,与你我都有一面之缘,实是个不可多得好女子,便是你,想必也不愿她嫁与这种人。我是曾想过叫这厮消失,但却不能这么做,于己来说倒是一了百了,可于关小姐来说,却是大大不利,试想一个未出阁女子,连着两个有过婚约男子都惨遭不幸,一个是险些摊上杀头之祸,一个却是身首异处。人言可畏,于女子来说实是……”
王取摇摇头。
“查,定要查个清楚明白,事已至此,只好见机行事。”
王取抬起头,眸子里满是忧色,却又异常坚定。“你提到疑点,查个明明白白,才好结案。暂将此事按下,待水落石出后,如何行事再议。”
说到底,邝贵死,王取只要个结果,并不一定要替他报仇,所以梁祈是事还是要请示督主才好进行下一步。
冷临见王取不似说谎,且也没必要说谎,西厂人之间没有秘密,再说即便是王取派了人威胁到邝贵人身安全,那也是无所谓。左右人已经被梁祈所杀,王取丝毫不会有事。所以,暂且相信王取话,邝贵死前怪异行为还要再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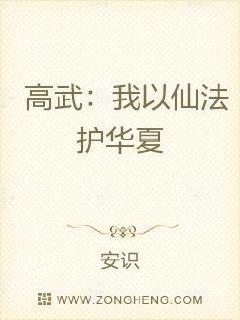
![[综漫]外挂是美食小游戏](/img/18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