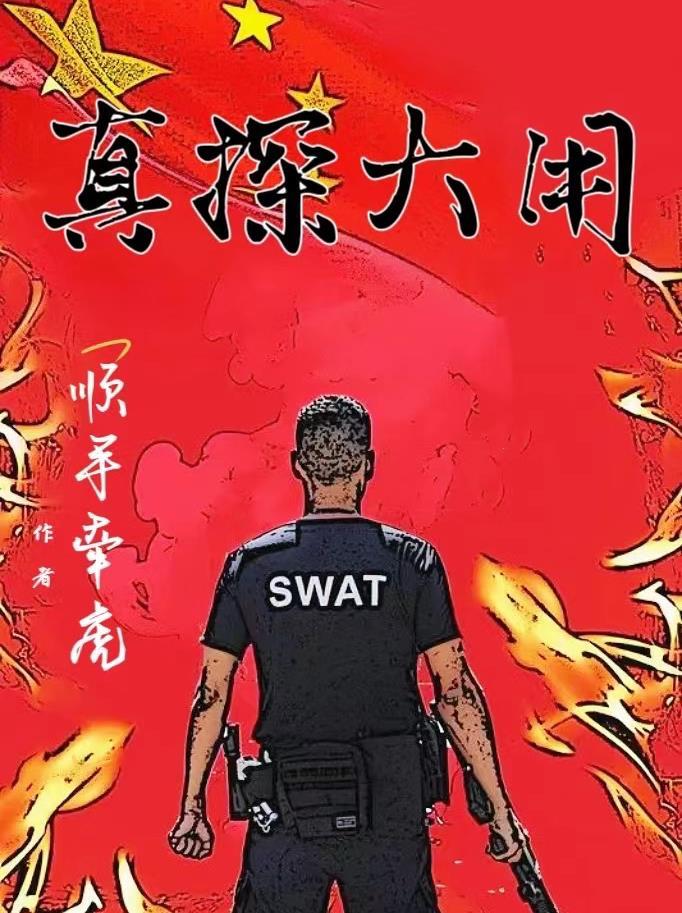爱上中文>海棠寄疏雨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等热闹完,宋宜要回帐内的时候,刘昶半路拦下了她,他今日出尽风头,神色得意,但见着她,又谨慎了几分,讨好道:“文嘉,方才在前头打猎的时候,见着两只小家伙,营中无聊,给你解解闷。”
手底下的人适时拎上来一只笼子,里头是两只小兔子,他道:“原以为此处没这些小玩意儿,谁知方才碰巧遇见了。这两只小家伙,看着乖巧,跑得倒挺快,叫人追了好一段才追上呢。”
他说得尽兴,伸出手指去逗那两只正在吃草的兔子,一抬眼见宋宜神色寡淡,兴致下去了几分,将那笼子接过来,讪讪往地下一放,“你别当是我送的就成了,闲着没事解解乏也好,你也不爱热闹,瞧着怪冷清的。”
他说完便走,跟在后头的人也赶紧走了,留下灵芝左右为难,“县主,这东西要带回去么?”
宋宜低头,那两只小玩意儿全然忘记了方才被人四处追赶的慌乱,安安静静地蹲在笼中,只有嘴角的翕动才让人觉出几分生机来。她伸手出去逗了逗,那兔子却并不理她,只是噙着草往后退缩了一步。
灵芝骂道:“连个畜生都不长眼。”
宋宜却笑了笑,“不近人情的东西,挺好的。只是他怎地又突然殷勤起来了,好一段时间没搭理过我了。”
朝宴那晚,刘昶同她已将话说绝,她以为按他的性子,自然只可能再来阴的,不会明着来受冷脸,不想今日竟如此古怪。但她没琢磨出什么来,只好吩咐灵芝:“叫人饲养着吧,东宫殿下赏的东西,敢随便扔么?”
灵芝无言,默默叫人将笼子拎起来,带回帐中。
宋宜病刚好全,又受了日晒,下午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如何也不肯再从帐中出来,灵芝瞧得有些怕,问:“县主可是当真哪里不舒服?”
“你这问的什么话?”
宋宜白她一眼,“叫别人听去了还说我托大不肯赏面子,今儿来的人,有几个我敢不给面子的?”
灵芝认错,“奴婢失言,那奴婢去回潘公公一声,请个太医来瞧瞧?”
本来就只是两三日功夫,又在京郊,随行御医只带了一两位,请起来也麻烦,宋宜摆摆手,“让我躺会儿便罢。”
灵芝应下,要退去外面,宋宜又道:“灵芝,我这心里头总不踏实,总觉得没好事。”
灵芝宽慰道:“猎场上,禁军多着呢,巡防严密,不比外头,县主安心。”
这股子不踏实持续了好一会子,宋宜半醒半梦,被魇住好几次,额上汗珠一直细密没断过。灵芝瞧得心惊,试探问:“县主又做那个梦了?”
雪地红梅,焦急的夫人,风尘仆仆归来的大将,与一樽碎玉。
这梦宋宜这几年反反复复地梦见了多次,宋嘉平寻了好些人来看过,各种法子都试过,也总不见好,隔一段时间便会梦见一次。她问过宋嘉平数次,他都只说:“没这回事。那玉是外头寻的,虽然只有一半,但料子甚好,便带回来了,不过是你梦里的场景,哪能当真?”
她问了几次,宋嘉平以相同的托辞答了几次,她也就信以为真了。可如今,这玉……她忽地想起来,这玉已不在她手上了,她问灵芝:“当日罚没的东西呢?”
“奴婢回府后听闻,当日圣上赏赐一下,王爷不在府上,世子也不好再说什么。按规矩,如今应在户部,或许早花出去了也不定。”
宋宜思索了好一会,问:“灵芝,仪门那处枯井,是哪一年填平的?”
灵芝一怔,仪门处确实有处枯井,但时日已久,她比宋宜大上几岁,当时还算记事,但宋宜那会年纪很小,按理不应记得此事,她犹豫了下,老实答道:“得有十多年了吧,听说有婢子跳井摔没了,夫人说晦气,王爷便命人填了。”
宋宜琢磨了下,那梦很短,又模糊得紧,她旁的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走路说话还算顺溜,起码已是两三岁的光景了,于是吩咐道:“回去记得问问,十一年到十五年这几年间,哪几年冬日里我爹在帝京没去外头的。”
“不过是个梦罢了,县主何必记挂?”
灵芝替她斟了杯茶,扶她起来喝了。
宋宜醒了神,才道:“每次梦见这事,醒来便要心悸好半日,我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以前觉着这事是小事,我爹也没放在心上,就算了,但我现在总觉得奇怪,查查放心。”
灵芝应下,又伺候她歇下了。待晚间,燕帝亲自设宴,不能托辞不去,才将宋宜叫了起来。
宋宜梳整完毕到的时候,大家都已到齐了,她自觉惭愧,捧了杯酒说要赔罪,燕帝今儿高兴,免了她这遭,“今日难得尽兴,不讲虚礼。”
她倒是讨了个好,但那股不踏实的感觉又强了几分,席间赔着笑,愣是没心情进半点食。
宴到一半,燕帝说乏了,先走一步,让在座尽兴,晚点命潘成赏东西,人人有份。他既开了口,宋宜自然不好先走,只好干坐着看众人行酒令,刘盈过来拉她,她也回绝了,“你也少喝些,一会子醉了,不比府上方便。”
刘盈冲她瘪瘪嘴,“你就是规矩多,老这么端着干嘛?”
宋宜没来由地一笑。
刘盈只觉莫名其妙,又端着酒杯去同她那群堂兄弟玩乐去了,“懒得搭理你。”
等到宴差不多散了,她坐久了,浑身不舒服,灵芝扶着她回了帐中,重新替她煮了新茶,她饮完一杯,口干舌燥之感不再,才觉得浑身舒坦了些。
灵芝伺候她梳洗完毕,问:“县主现在歇着还是待会儿再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