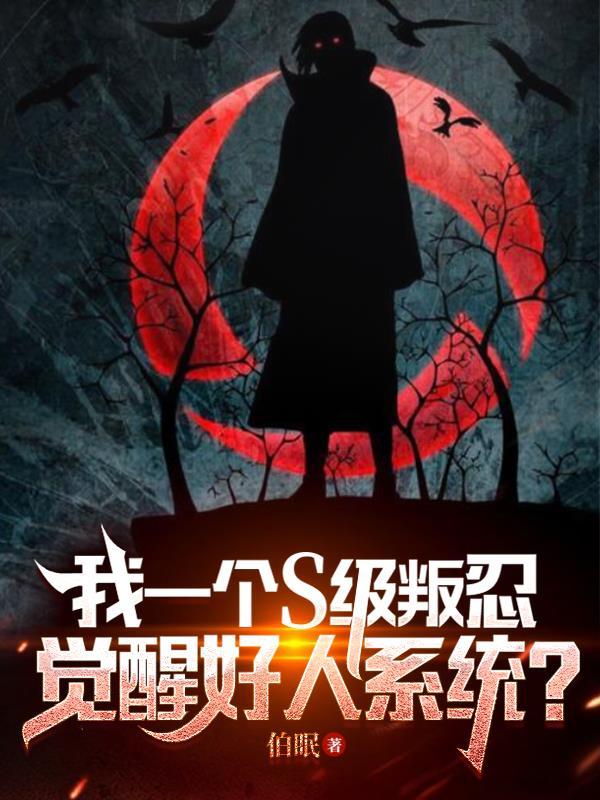爱上中文>流光飞影的意思 > 变革年代一幅幅底层浮世绘(第1页)
变革年代一幅幅底层浮世绘(第1页)
※变革年代一幅幅底层浮世绘
——以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作品为例
一个国家的崛起,在于经济,也在于文化。经济是生的保障,文化则是活的意义所在,这是真正的生活。
贾樟柯拍了十多年的文艺片,其中一部短片《小山回家》(1995年),七部剧情长片《小武》(1998年)、《站台》(2000年)、《任逍遥》(2002年)、《三峡好人》(2006年)、《二十四城记》(2009年)、《海上传奇》(2010年)、《江湖儿女》(2018年),一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凭借高品质与高口碑,受到国际各大电影节的好评和认可,在欧洲、北美培育了自己的观众群,这八部影片都注重影片气质。
学者梁从善认为:“贾樟柯的电影有灵魂,而且有着清澈、悲悯的灵魂。他的电影主要描述人物在社会变革背景下的迷茫和选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大地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场深刻的变革,必然带来社会的震动、太多的个人命运的转变,只有不停地主动求变,才能够不被这一变革潮流所改变。记录下变革中悄然发生的一切,应该是中国所有艺术家的历史使命。贾樟柯在他的电影中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变革
中那些动荡的灵魂。他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命运,呈现他们的痛苦、迷茫、无所适从,以及在时代中的命运变化。可以说,贾樟柯的电影从一个重要、独特的角度,为中国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受众提供了变革年代的一幅底层浮世绘。尽管受众在他的电影里很难看到他指明的人生方向,但他电影里的人物,良心没有泯灭,道德没有沦丧,人性没有扭曲,也就是说能看到爱心、感恩之心、责任感、善良,那种小小的爱心和善良让人心安,而爱心和善良就是人类的希望。不同于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主题注重反思历史,贾樟柯电影的主题注重人文关怀,并且深藏在每一个镜头中,它不是冷冰冰的教条,而是泛着体温的守望;它不是俯视的怜悯,而是平视的尊重。
《小山回家》,开启了中国独立剧情片的新模式
1995年,贾樟柯拍了短片《小山回家》,以极为写实的手法,再现一个打工者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老家前的所遇所想,表现了在农民工大量进城背景下,主人公在城市里的遭遇和状态。虽然只是表现一个人在特定时间段的生活,却极具代表意义,使人可以一窥农民工这个阶层的真实生活。故事讲述在北京宏远餐馆打工的农民工王小山,被老板赵国庆开除。回家前,他找了许多从安阳来京的同乡,有建筑工人、票贩子、
大学生、服务员等,但无人与他同行。他落魄而又茫然地寻找尚留在北京的一个又一个往昔伙伴,最后在街边一个理发摊上,把自己一头城里人般凌乱的长发留给了北京。
这部片子确立了贾樟柯电影的基本风格:纪实风格的长镜头,以日常细节呈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底层生活才有的氛围,小人物的卑微命运。《小山回家》用呈现现实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独立剧情片的一种新模式。
《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拍摄手法
《小武》是贾樟柯的首部长片电影,呈现了一个小偷的生活、爱情及内心世界。故事的最后,小武被铐在广场上,他在越来越多的围观者中,渐渐低下了头。贾樟柯的镜头忽略了小武羞愧的表情,而把大部分镜头给予了那些越来越多、冷漠麻木的看客。在以小武为中心的看客人群圈里,贾樟柯仿佛在画着一个大大的句号,以此不仅完结这部影片,也完结了小武这段并不圆满的生活历程,完结了看客也被观众看的命运。
《小武》是一部追求小而实的电影,将目光投向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卑微个体,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境遇给予关注和关怀。
法国《电影手册》评论电影《小武》,说其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拍摄手法。贾樟柯用拍纪录片的手法来拍剧情片《小武》,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些风格延续在他
后续的电影作品中。
《站台》,被自我和社会双重流放的尴尬境地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
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
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
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
哦孤独的站台
哦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
电影《站台》的创意来自这首歌。从片名来看,就是火车周而复始地来来往往,表现的是人的生存困顿和精神守望的无间轮回。《站台》以缓慢而几近纪录片风格,叙述了一群剧团里的年轻人,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开始自谋生计,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巡回演出,结束了以往平静、安逸、自恋的生活,开始品尝酸甜苦辣、茫然若失的滋味。画面之真实,节奏之缓重,情景人物之似曾相识,使人不由得感慨不已,生活没有一劳永逸,要想不被抛弃必须自己争气。如此准确、深刻而连贯地影画中国底层民众随着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而起落沉浮,难能可贵。贾樟柯说:“《站台》这部电影的主体是人,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等人既组成了一个群像,同时又通过每一个人的经历,反映了这个群体在时代中的遭遇——自卑、自尊、自怜、自恋,以及陷入被自我和社会双重流放的尴尬境地。”
这些心理和遭遇,并不是以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或者别的重要事件中来体现,而是以社会底层的小
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面向来体现。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工团的作用逐渐消失,“最为基层的知识分子”
首先受到冲击,产生了普遍的挫败感和理想破灭。同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潮流涌动,使文化尤其是边远小城的文艺生活开始以市场、大众趣味为衡量,去深度化的倾向使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大大减少。《站台》中的文工团团员代表的基层知识分子,就像数量庞大的蜉蝣在时代浪潮中浑浑噩噩,他们的状态已经初露20世纪90年代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所颠覆的端倪。以感性愉悦为基本审美特征的普通大众文化必须去深度化,如文工团后来演出节目的庸俗化,普通大众在消解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
《任逍遥》,一幅小城市年轻人的漫画
“任逍遥”
在影片《任逍遥》中似乎只充当一个时刻存在的标签,或者是黑色幽默的标题。影片的用力之所在,当然不会是对庄子名篇进行疏证,来解释什么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戴着手铐的郭斌斌,在公安局里唱起《任逍遥》这首他最拿手的歌:“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更像是关于“没心没肺地想干甚就干
甚”
的黑色幽默。导演的幽默显然不在于所谓反讽或者道德说教,而是从更深处揭示那些卑微的人和他们卑微的生活与逍遥无关,实是无奈之举。
《任逍遥》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如何在庸常的生活中被情绪控制走向犯罪道路,提供了一幅小城市年轻人游手好闲、寂寞空虚的画图,面对变革,他们的不适应和迷茫,终于使他们稀里糊涂地走上了犯罪道路。《任逍遥》也许是导演贾樟柯借两个年轻人的无奈青春,表达一种无法言说的郁闷。
《三峡好人》,平静中流淌出荒诞
影片《三峡好人》以平静的视角拍摄拆迁过程中的三峡,并以维系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幸福标准的“烟酒茶糖”
这四样东西来表现拆迁过程中三峡人民的生活。演员用质朴的表演、导演用新奇的艺术手法共同传达出努力生活的渴望。影片散发着不浓不淡的人性关怀,导演与演员用同理心浅浅地表达出社会现实中普通老百姓“烟酒茶糖”
式的生活状态。
《三峡好人》采用的是三段嵌入式的双线索平行叙事方式。首先是来自山西的韩三明寻人的故事,中间插入了同样来自山西的沈红找人的故事,最后又回到韩三明寻人的叙事中来。故事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索是寻回爱情,讲述山西汾阳的煤矿工人韩三明与麻幺妹的非法爱情故事,韩三明在十六年前买回了
四川媳妇麻幺妹,麻幺妹刚怀孕,就被公安局解救回四川了。十六年来韩三明和麻幺妹天各一方。这一次,韩三明去正在拆迁的三峡地区寻找他和麻幺妹的女儿。因三峡拆迁工程正在大规模进行,麻幺妹家所在的县城早已被淹没在水底,麻幺妹的哥哥对韩三明也不友善。经过几次三番折腾,韩三明终于见到了麻幺妹,两人决定正式结婚,成为合法夫妻。另一条线索是舍弃正当合法的婚姻,山西太原的护士沈红到奉节寻找两年没有联系的丈夫郭斌,见面后发现他们之间有隔阂,两人的感情不可能回到从前,沈红决定和郭斌离婚。影片双线索叙事一直是平行的,自始至终都是两个独立的故事,它们相互不影响,没有交叉,最后集中于叙事情节的高潮,这种诡异的叙事方式,如同那座没有建完的移民纪念塔像火箭一样升空、飞碟(UFO)划空而过,让平淡的剧情进入高潮,耐人寻味。
《二十四城记》,人与“单位”
的关系
《二十四城记》作为贾樟柯的第六部剧情长片,用真实与虚拟融合的方式,用八个人的记忆,勾勒出中国五十年工业厚重的历史。曾经的繁华荣耀,随着时光流转与时代变迁渐渐褪去耀眼的光环,留下的是无尽的落寞与慨叹。420厂(成华集团),一座从东北迁至四川的军工厂,在特殊年代它是无数人羡
慕与自豪的所在,然而和平气息与体制改革将它的光鲜逐渐销蚀。在经济浪潮冲击下,它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而今旧厂址易作他用,一片现代化的楼宇将拔地而起。
从1958年到2008年,由陈冲、吕丽萍、赵涛饰演的三代女性的故事朴实动人。吕丽萍饰演第一代女工;陈冲饰演的小花,是外号“标准件”
的厂花;赵涛饰演的娜娜,一直试图摆脱家庭和工厂的束缚,渴望尝试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