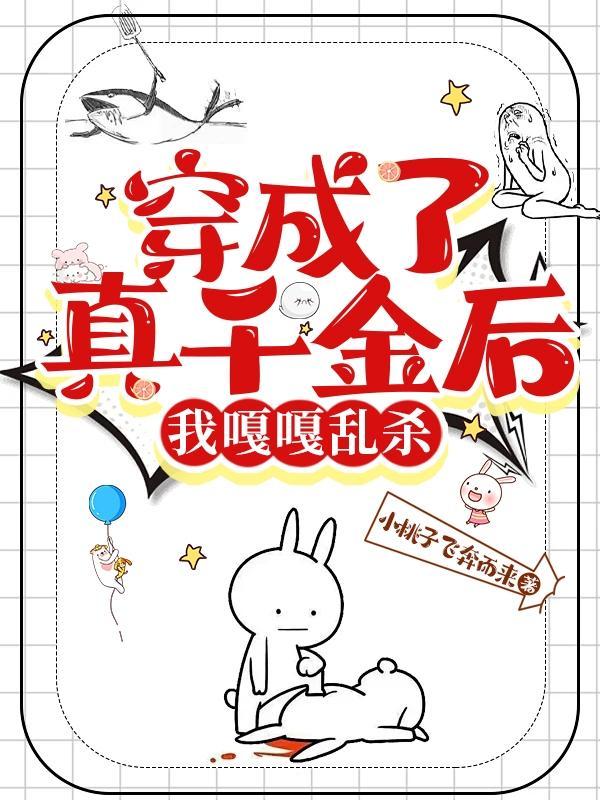爱上中文>无人区玫瑰歌词 > 微(第4页)
微(第4页)
周述眸中闪过一瞬惊喜,又迅速恢复,平静地问:“你见过我吗?”
程悉猛然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身边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周述这样闪闪发光的人,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记错了。”
周述没吭声,拿着手里脏掉的纸巾和纱布,背过身去扔进垃圾桶。
程悉看不到的地方,他的嘴唇疯狂颤抖,俊俏的五官竟然显得有几分狰狞。冷淡的眼睛中迸射着奇异的光。
他紧紧狠狠攥紧拳头,本就不显血色的指尖因发力而更加苍白。
咬了咬牙,周述艰难开口:“……你走吧,今天会诊结束了。”
程悉只觉得有点奇怪,穿好裤子下了诊台,跟医生道了句谢,轻轻地关上了门。
周述沉默地站在原地,纯白而空大的诊室里,只有他一个人。
除了他自己的心跳,再听不到别的声音。
周述低着头,面无表情地脱下白大褂,离开了这里。
……
回到别墅里,天已经黑透了。周述“啪”
地一把拍开门口的一盏灯,跌跌撞撞地跑向阁楼。几次狠狠撞到墙壁,周述却像感觉不到疼一样,疯了似的朝楼上跑。
他哆哆嗦嗦地掏出钥匙,昏暗的阁楼终于被照亮了一点。
狭小阴蔽的暗红色空间内,只有一张铺着暗红床单的单人床,以及一枝插在花瓶中,早已枯萎的红玫瑰。
潮湿腐朽的房间中,弥漫着逼仄、阴暗的气息。
满墙都是程悉的照片,自拍、偷拍,各种角度,各种穿搭……以及裸体。
周述痴迷地埋进被褥中,以一种几乎狂热的眼光深深吸了一口气。鼻尖萦绕一股腐烂的玫瑰气味。
如果此时,程悉也和他亲爱的周医生做同样的动作的话,他就会惊奇地发现,这股味道……正是他高中以来一直缠绕在他身上,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他自以为的体味。
神情宛如吸食鸦片一样的周述在糜烂而绚丽的味道中平静下来,头仰起,沉默地盯着暗红色玫瑰纹的顶板,又掏出手机,无力似的拨了过去。
……
前一天在医院做过前列腺按摩,后穴的瘙痒稍微抑制住了点,程悉这几天精神都好了很多。
至少不用明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做那档子事,体力消耗少了,睡得也早了。
所以第二天程悉就起了个大早下楼晨跑,顺路买了一份豆浆油条,心情愉悦得一路都在吹口哨,连卖早餐的大爷都被他的好心情感染,笑呵呵地多给他夹了根油条。
程悉换下运动服,穿上正装,大步迈进公司。
虽然他年纪不小了,但是因为中途换了几份工作,现在在这家公司还算是个菜鸟职员,他又是个性子直的,平时
没少被前辈教育。使唤他干这干那的,他心想算了,图个安稳,忍气吞声地照做了。
今天也是如此,同事赵姐非得让他替自己去经理办公室送文件。今天心情不错,程悉也就没跟她一般见识,依然身形挺拔,不卑不亢地进去了。
赵姐在他身后松了口气,又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目送他。
程悉这经理年纪比他还要小,二十出头,本来应该是个白白净净的男大学生,被包养之后总跟金主撒娇要自己开公司玩玩。工作能力一般般,但毕竟是小情儿,长得倒是肤白貌美,娇滴滴的,有些雌雄莫辨的美。
“今天跟莫哥的兄弟谭总晚上有个局,酒局散了之后,我陪莫哥,你去陪谭总。”
莫哥便是他那金主。
程悉瞬间明白所谓“陪”
是什么意思。
攥握的拳松了紧,紧了松,又像是无力地垂了下来。程悉皱起眉头:“经理,我……硬邦邦的,一点都不好看,也不怎么会说话……”
经理仰面靠在老板椅上,来回慢悠悠地转着圈:“人家点名要你,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你也是挺有自知之明……行了,必须去,不能扫了莫哥和谭总的兴。这笔生意做不成,你知道要赔多少吗?”
程悉偏过头去,没有吭声。
经理漫不经心地拨弄起自己的指甲:“你要不去也不是不行,辞职吧。你不是我的员工,我自然也没办法逼你。”
染成浅金色的头发靠在椅背上,在阳光下又转了一圈,嗤笑道:“我都忘了,你这么清高,这么有原则的人,不可能在意丢掉这份小工作吧?……嘶,但是也未必,听说你天天被要债的找上门,房租也要到期了?没有工资,就快活不下去了吧?啧啧啧,真可怜。”
程悉咬紧了牙。
经理见他居然还能忍下来,抬头思考了一会儿,又天真地看着他:“……你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吧?你爸失踪了,你妈……我没记错的话,因为你妈的病你又欠下好大一笔钱吧?虽然她已经死了,但是死得那么不光彩,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给你妈的脸面考虑考虑吧?”
程悉瞬间冷下脸,正过脸,剑一般锐利的目光冷冷地射进经理的眼睛。
明明眸子里盛满了怒火,却叫人不寒而栗。
经理轻咳一声,硬着头皮继续刺激他:“……你也不必傻傻守着什么原则啊底线啊,毕竟混到你这种地步的人都舍弃了所谓尊严的。没有钱,没有权利,你哪有尊严……”
程悉快被气笑了。他扪心自问,工作绝对尽职尽责,对同事上司也是礼貌有加,为什么这种事情总是发生在他身上?从父亲破产欠债消失不见、母亲自杀未遂后发疯后,他好像……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他真的感到快乐了。
他把只属于自己四个月的办公桌收拾干净,那里瞬间空了下来。
临走前,程悉回了头。
一如他没来过一样。
从公司出来,程悉早已没了上午把咖啡从经理脑袋上当头泼下的气势。捧着被水杯、文件夹、小盆栽装满的箱子,他到便利店里买了面包和水,草草解决掉午饭后,一个人走在车水马龙间。
喧闹声将他彻底与周围隔开,归属感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