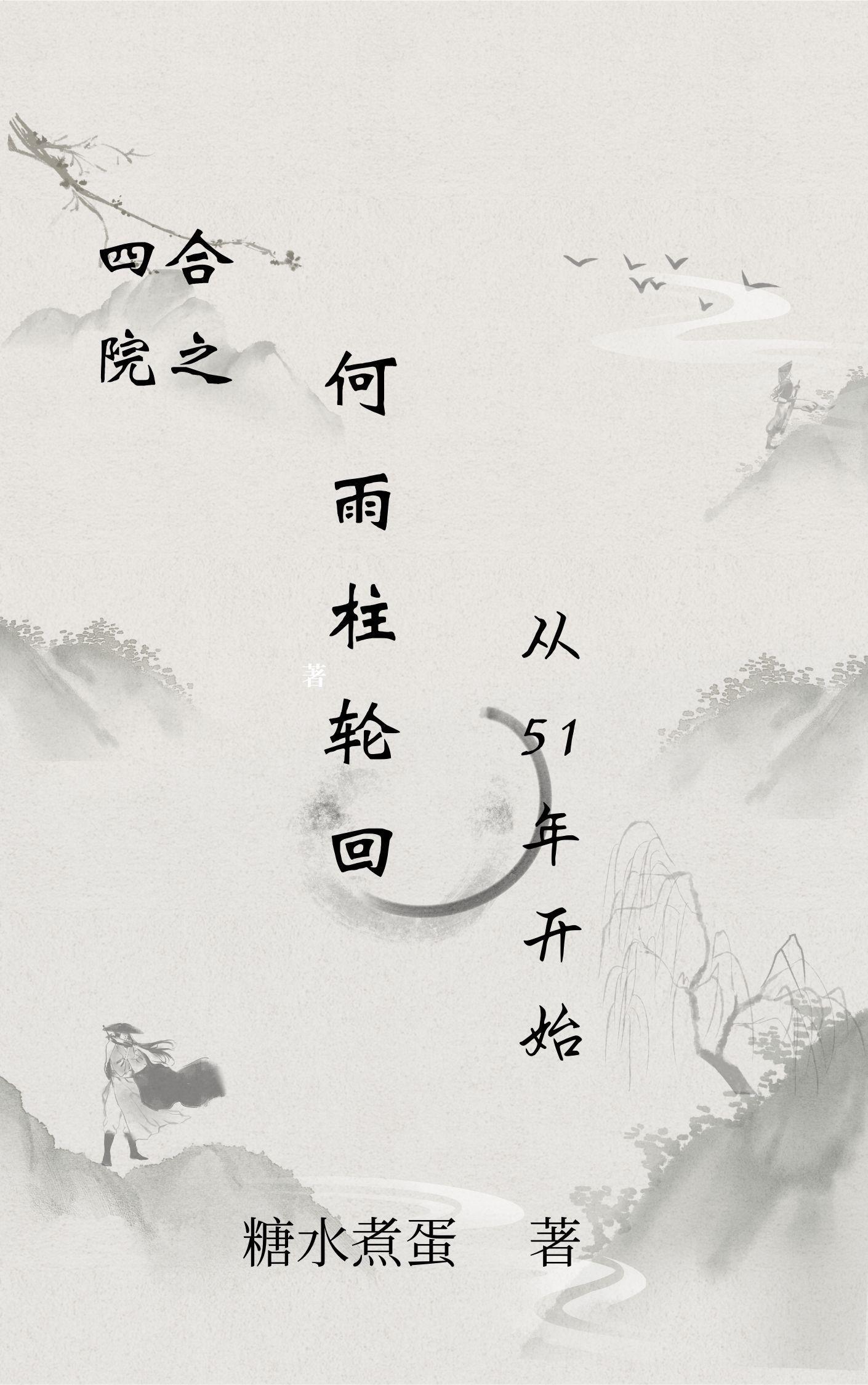爱上中文>农家长嫂种田忙 > 第二十章红薯(第1页)
第二十章红薯(第1页)
春归放了话,知行立刻点了头,房里本就有现成的笔墨,他收起平日吊儿郎当的模样,只片刻便写了两份,用词决断,下笔利落。写完后拿给祁佑看过后便出了门。
祁佑偏过头看向春归:“春姐,你能留下我便好,其他的不必再思虑也不必想着替我讨回什么。那份断亲书压着,咱们家能稳妥地过上些日子。”
“我能忍,一切,便等到来年院试吧。”
他眼里俱是平静。
等他考中了秀才,世易时移,那份如今只能表明他决心的断亲书到时便会成为一把高悬的尖刀,若有了造化,中举,科举,这把尖刀终有一日会压得程家喘不过气。
春归平静后便想明白了其中一二,她看向床上这个坚韧的少年,摇摇头抿了抿唇角。
当日他被迫分家,程家本家不作为,今日他分了家,程天保还能想出这怨毒心思,
这断亲书收得不冤。
知行脚程快,只过了一会儿便跑了回来,手里空空,显然是都送出去了。
春归连忙问道:“他们怎么说?”
知行喝了一大碗水后才道:“嫂子,里正叔说他都明白了,今日他让祁佑在咱家住着不是随口说的,日后便托你多照顾他。”
“那程家族长呢?”
知行脸一黑:“那老头子看了断亲书后骂了一句不孝,我便直接走了。”
听到这儿春归冷笑一声,今日发生这么大的事儿程家迟迟没来个人出面,她就该知道程家多半
是些迂腐不作为的老封建了。
“行,就这样吧,那断亲书没摁下手印也不管了,如今只当祁佑是咱家的。”
她当即决断。
连着几日,里正托里正媳妇儿又送药材又送吃食,想来心里是万分歉疚的。春归也照着收了,送的都是祁佑如今需要的,也都用在祁佑的身上。
李大夫也时常送来草药,那日摔裂的伤口总算又恢复了些。这些时日,蔡氏也怕打扰祁佑养伤,没将小宝送来。
直到祁佑伤口明显愈合,春归心里这口气才渐渐地平了,只是再也不敢留他一个人在屋里,知行知平知敏三个也是如此,轮着进屋陪着。
这样好了大半后,春归才让几个孩子继续背书的背书,练字的练字,照例还是在祁佑的房里。
-
几日后蔡氏也送了小宝过来,送来时知敏正好背完一整轮,蔡氏看过祁佑的神色也好了许多,拉过春归问道:“听程家村的人说,祁佑给送去了一份断亲书?”
送去那日,春归便知道,这事儿不久就得传遍了。她点头道:“送了。”
蔡氏面上大快:“就得这样!还真当祁佑是面人儿呢!”
“这半月程天保那对丧尽天良的夫妻连门都不敢出,那程桂香嘴巴硬,硬说是祁佑腿脚不好了,那断亲书的事儿传过来后,她大气儿都不敢出了,就怕来年三月祁佑中了秀才,本家把罪怪到她头上,如今也跟程天保那一对儿似的,躲屋子里七
八天了。”
这些天村子里的风向倒来倒去,有的骂程家人坏心肠,也有的说祁佑做得太多,还有的照例闲话几句,说祁佑住柳家说出来不好听。
蔡氏全都门儿清,春归听了也不在意,风头正劲的时候,管不住别人的嘴。
她往窗外扫了一眼,院儿里的番薯苗栽下去已有两月,长得十分茂盛,估摸着也快成熟了。这些时日杂事儿多,她倒是忘了这一茬。
两月前知平喝着第一口糖水时高兴的模样她一直没忘,这些时日家里经了太多事,虽不说,可这些孩子心头到底还是苦涩的,这样想着,她偏过头道:“蔡姐姐,你家里可还有红糖?”
这番薯长成了,正好能做些红薯糖水给几个孩子甜甜嘴。
蔡氏闻言大方道:“明日我给你送些,不必给我省着,你也知道我那老娘有一身本事。”
“如今我那弟弟成了婚,大体上算是分了家,我那老娘心疼小宝,便三不五时地送些糖过来。”
蔡氏娘家除了一对爹娘外还有一个弟弟弟妹,今年年初刚成的婚。老爹老娘便有心力心疼这个年轻丧夫的女儿和外孙,大旱过了之后便立刻重新翻种了一季甘蔗,再过约莫一个月的样子便能收上一季,家里的糖确实多着呢。
如此春归也没推辞。
又过了半月,祁佑已能下地走几步,一家子头顶的阴云才算彻底过了。
春归的番薯又长了些,野番薯也有野番薯的优势
,长势十分喜人,已经长出地里一大圈,颇有向草棚那儿长的趋势,引得棚里的小鸡时不时地啄上几口。春归赶紧围了个栅栏,将长出去的藤移了回来。
她擦了擦额角的汗,这一块地下一季的番薯怕是不够长的,隔壁祁佑的院子空荡荡一片,照着里正的意思,祁佑便是在她这儿住下了也不要紧,她便瞄上了隔壁,看能不能在他那儿开出一片地来。
如此想着,她便进了屋。
这半月,李大夫来换过几次药,伤口只有些肿,旁的问题倒是没有。
屋里祁佑正和知行两人题诗,这些时日她又画了几副画样儿,知行作诗的兴致高涨,两人各自写完后便互相斧正。春归也乐得看他们如此,明年二月份才开私塾,如今还有两月时间,若是每日都是温习功课不免无聊。
见她来了,祁佑放下笔,知行连忙将写完的诗词推过去,一脸得意:“嫂子,你看,我们写了大半了!”
春归不懂这些,随便翻了几首,挑了挑眉:“我诗词倒是看不出好不好的,不过这字嘛。”
她抬眼瞥了一瞥:“柳知行,你怎的写得如此急躁。”
一张纸一分为二,一头是知行写的,一头是祁佑的笔墨,祁佑那端工工整整,知行写的那一方字迹却越来越潦草。
春归目光满是不赞同,又翻了几页。知行笑嘻嘻地将剩余的纸拿回来:“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春归不管他了,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