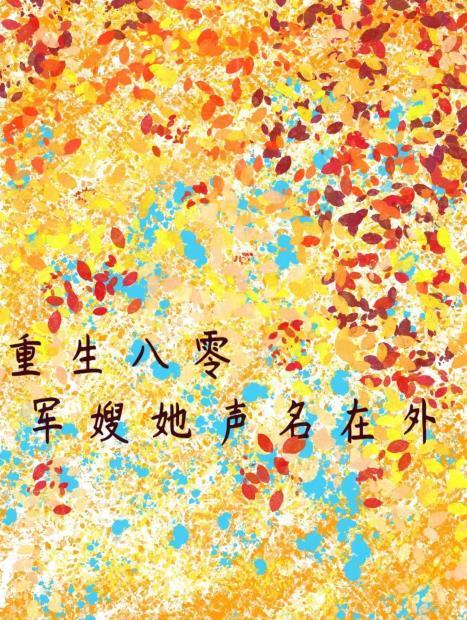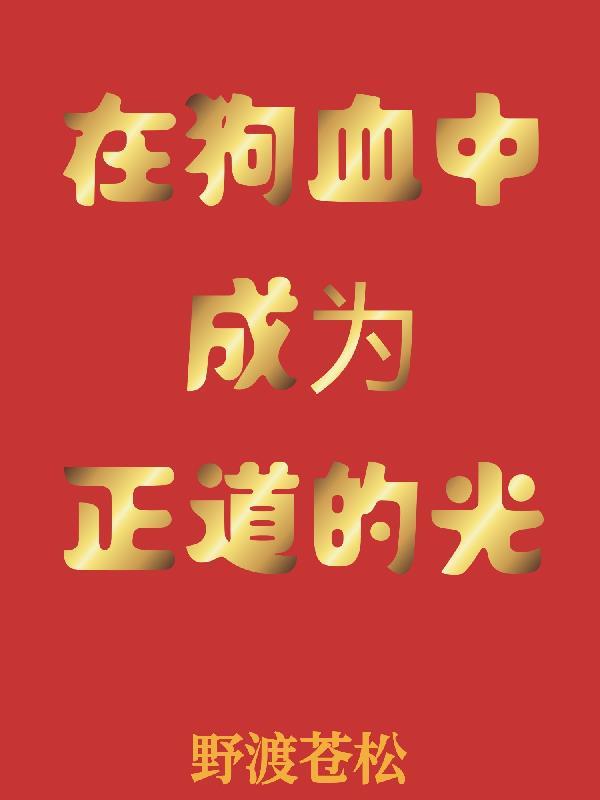爱上中文>民国赤色革命从阿Q正传开始作者我是柠檬精啊 > 第54章 夏瑜的信与决定去未庄的革命青年(第3页)
第54章 夏瑜的信与决定去未庄的革命青年(第3页)
王安达显然非同赞成何怀德的话。
一说完,他忽然叹息一声:“不知道黄先生怎么样了。”
何怀德拍了拍王安达的肩膀:“黄先生的伤并不重,又有东洋的名医给他诊治,那点伤势没肯定早就痊愈了。”
话题一转,他接着说道:“那位送信过来的信使被我安排在我家休息,回去之后,我就向他打听夏瑜的近况,再寄一封信去催一催他,让他尽早把接下来的内容写好寄过来。”
两人聊一会儿后,又把那封信看了两遍,并且剧烈地讨论了一阵。
直到傍晚时,何怀德才离开。
关上门,王达安便迫不及待地抄录起了夏瑜的信件。
即使已经把信件上记载的这段英吉利的历史看了好几遍,在抄录信件时,他依然时而出嗟叹,时而在有所得时露出恍然的模样。
他与何怀德之所以对上面所叙述的英吉利的革命史入迷,不仅是因为信件上所用的叙述历史和分析历史的方法新颖奇特,而且更多的是与他们现在的切身经历有关。
几个月前,他们参与的起义被清廷镇压,致使死伤无数。
连起义的领导人黄轸先生也不得已去了境外养伤。
革命进入了低潮,使得王安达这样的有志青年开始进行反思——
这次的行动为何会失败?
清廷腐败且懦弱,既然如此不堪,为什么他们却始终无法推翻清廷?
既然上次起义失败,那么下一次又该怎么进行起义活动?
夏瑜记叙的那段历史虽然与中国无关,却给了迷茫的他们一种反思的方法,一种思考的方式,使他们的思路变得更为开阔。
故而,他们才会如此看中这上面的东西,如此渴望看到未尽的内容。
写着写着,觉得自己的思路清晰了许多的王安达忽然又看向夏瑜写给两人用来问候与解释事情因由的信件,视线在某一段话停留了许久——
“徐先生在未庄隐居多年,却无时不在关注我们的事业……对方向有清晰地认知……对我的问题总是能给我一个合适的答案……”
第二天一早,何怀德敲开门,见到的是双眼布满血丝,却精神奕奕的王安达。
“你……你这是怎么了?”
何怀德开玩笑道,“难道昨晚一夜没睡?这可不像你……”
王安达忽然打断道:“我要去找夏瑜!”
“什么?”
何怀安愣了愣,“安达,你……你要去找夏瑜?”
“不错。”
王安达语气坚定,“我的伤势早就好了,留在这里也没有用,还十分危险,不如去看看夏瑜过得怎么样,再见见那位徐先生,也许会有所得。”
何怀德其实也想去见那位徐先生:“如果真像夏瑜所说的那样,确实应该去见见,可是……”
王安达伸出双手,按住了何怀德的肩膀上,认真说道:“怀德,这里有你就够了,我必须要去看看!”
“我也想去。”
何怀德推开王安达的手,“不如我和你一起去。”
王安达却摇了摇头:“怀德你留在粤城最好,可以随时等黄先生的消息,若是有事,也可通知我。”
“我去夏瑜那边看看,如果有所得便传信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