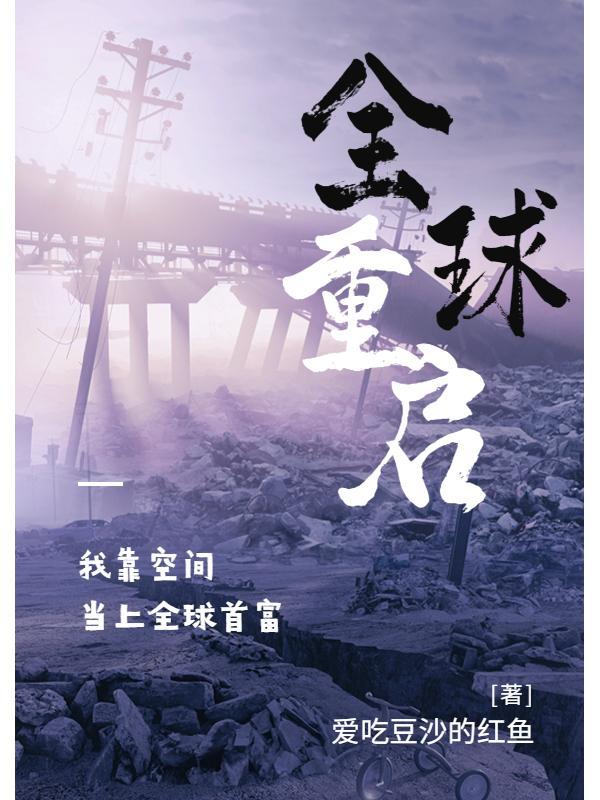爱上中文>腹黑小狂妃皇叔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无邪怔了怔,容兮已是戒备地将手扶上了腰间,随时可能要抽出那腰间的软剑,而那满头白发的男子,却是轻蔑地扫了眼容兮扶在腰间的手,然后将目光扫落在了无邪身上,贵公子一般向前朝她走来:“一个人喝酒着实无趣,我刚挖了两坛好酒出来,不如你陪我喝吧小鬼头?”
因被雪水打湿,几缕银白的发丝紧贴在脸颊上,衬得他的眉眼越发清俊,他快步朝无邪走来,连带着迎面而来的风都夹杂了些酒香,他嘴里说的是征询意见的话,可那口吻,却像只是纯粹要通知无邪一声罢了。
容兮哪里会肯,电光火石之间,就要抽出腰间软剑来,却见红袍翻飞,仅眨眼的功夫,竟将容兮死死点在了原地,拎起无邪就扬长而去了。
无邪忽然被拎了起来,脚下一空,冷风迎面扑来,整个人被那白发男子夹在了手臂下腾空略起,几个起落间,竟然轻而易举地出了皇宫,在宫墙后的一处杂乱枯草地将她丢了下来,嘴角微冷地上挑,阔步转身往回走了几步:“你倒是镇定,不惊叫也不曾被吓哭,难道不怕我对你不利?”
无邪的确是镇定,拍了拍屁股站起来,被数只猛虎围着的时候,她都不曾失声惊叫过,被一个人给拎出了皇宫,又有什么好吓哭的?
“你在皇宫里做什么?”
那人随意地往地上一坐,似笑非笑地慢悠悠答道:“自然是挖了几坛好酒,我见长生宫从来就没人往那去,便从四处搜罗了些好酒来,埋在长生宫里的那棵大树下,闲了馋了,便去挖几坛。”
“原来是惯犯。”
无邪“哦”
了一声,也慢悠悠地问了一句:“我为何从未见过你?”
“你?”
那男子红袍艳丽,穿在他身上,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潇洒,白发肆虐披散,更显得不羁了几分:“你还嫩了点,今日若不是见皇宫里有大事,更加无人有闲情管长生宫的事,便大意了些,否则哪轮得到你这毛头小子撞上刚挖了好酒的我?”
他也不问无邪姓甚名谁是什么人,看起来是真的目中无尘,丝毫不在乎这些繁文缛节,拍了拍身侧的空位,他示意无邪过来坐,无邪摇了摇头,他也不勉强,拎起一坛酒就朝无邪扔了过去:“毛头小子,便宜你了,今夜你我皆是闲人,不如彼此作个伴。”
那酒坛子忽然迎面就朝无邪飞来了,无邪心中一静,并不随意泄露,只装做被吓到了一般,连躲也不会,呆呆地睁大了眼睛。
砰!
就在那酒坛子即将砸向无邪面门之时,它竟在半空中忽然碎裂了开来,酒水顿时四溅开来,劈头从无邪脑门浇下,顿时将无邪浑身浇了个湿漉漉。
那正坐在对面的男子丢了手中临时捡起的石子,扫了眼碎了一地的碎片,摇了摇头:“枉费了我一坛好酒。”
话虽这么说,可他的神情却颇为豁达,宛如只醉心沉浸在风月山河之中,于世俗无碍无扰。
无邪被浇透了,又不曾运内力御寒,此时冷风又一阵呼啸而来,顿时将无邪冻得嘴唇都隐隐发白起来,手脚小心哆嗦着。
“喝一口。”
那男子忽然站起来,拎着只剩下的那唯一一坛酒朝无邪走来,将酒坛子凑到她嘴边。
无邪哆嗦着,闻言乖乖喝了一口,甘醇的液体入喉,身体却是暖和了些,他便又给无邪灌了一口:“再喝一口。”
接连喝了几口,无邪这才觉得浑身暖和,不再觉得发冷,便也不再哆嗦了。
只剩下一坛酒,他自然不能再全都给无邪了,两人席地而坐,你一口,我一口,今日初见,倒像是早已相识多年的老友一般,无邪亦不扭捏。
“你怎会突然去那没人去的鬼地方?”
他把酒塞给无邪,不以为然地问了句。
无邪喝了一小口,老实答道:“不过一时恰巧经过,你又为何将酒埋到了那里去?你认识二皇子?”
“那家伙不是已经死了?”
他又嗤笑了一声,口中对皇家的人无丝毫敬意,只似随口谈论起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般:“死人的地方自然不是活人的地方,那地方住不了人,只好留着给我埋酒了。”
无邪点了点头:“可惜了,我听我父王说,二皇子才华横溢,皇上甚至希望改立他为太子,若他还活着,竟来这卞国的君主许就是他了,可惜英年早逝。”
“做皇帝?”
他那如深潭静月般深邃惑人的眼似醉非醉:“那他还是死了好。”
无邪被噎了一口,不曾想这人的嘴竟是如此毒,卫冕也太张狂不羁了些。
似笑非笑地瞥了无邪一眼,他忽然说道:“小鬼头,莫非在你眼里,只有那至高无上的权势才是好东西?”
无邪张了张嘴,一时无言以对。
“看来你喜欢的也是那东西?”
他忽然笑了,也不知是不是在嘲笑无邪天真,可那嘴上却难得地没有打击她:“也罢,你就争抢那东西去吧,这么多人抢着,若是赢了,也挺有意思。你方才说了句‘父王’,看来你也是一个小权贵,可我只与享受得了风月,品得了美酒的人喝酒,你若与我谈,便不谈那无趣的事,只说风月之事。”
“风月之事?”
无邪重复了一句:“那你可知,那长生宫的主人为何忽然辞世?我听闻,他的尸身并未被找到,只葬了衣冠,想必当时以他的智计,没那么容易死,也或许,这死,不过是死遁?也许他也与你一样,厌烦那叫权势的东西,只追着风花雪月去了?”
“这猜测倒是大胆。”
那男子称赞了无邪一句,继而挑唇笑道:“我怎听闻,那长生宫的主人,曾也是醉心权势的人?否则纵使再是神童,若非醉心研读兵法政事,又哪里能得皇帝如此偏爱,竟然还一度曾向罔顾那立长立嫡的纲纪,要立他为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