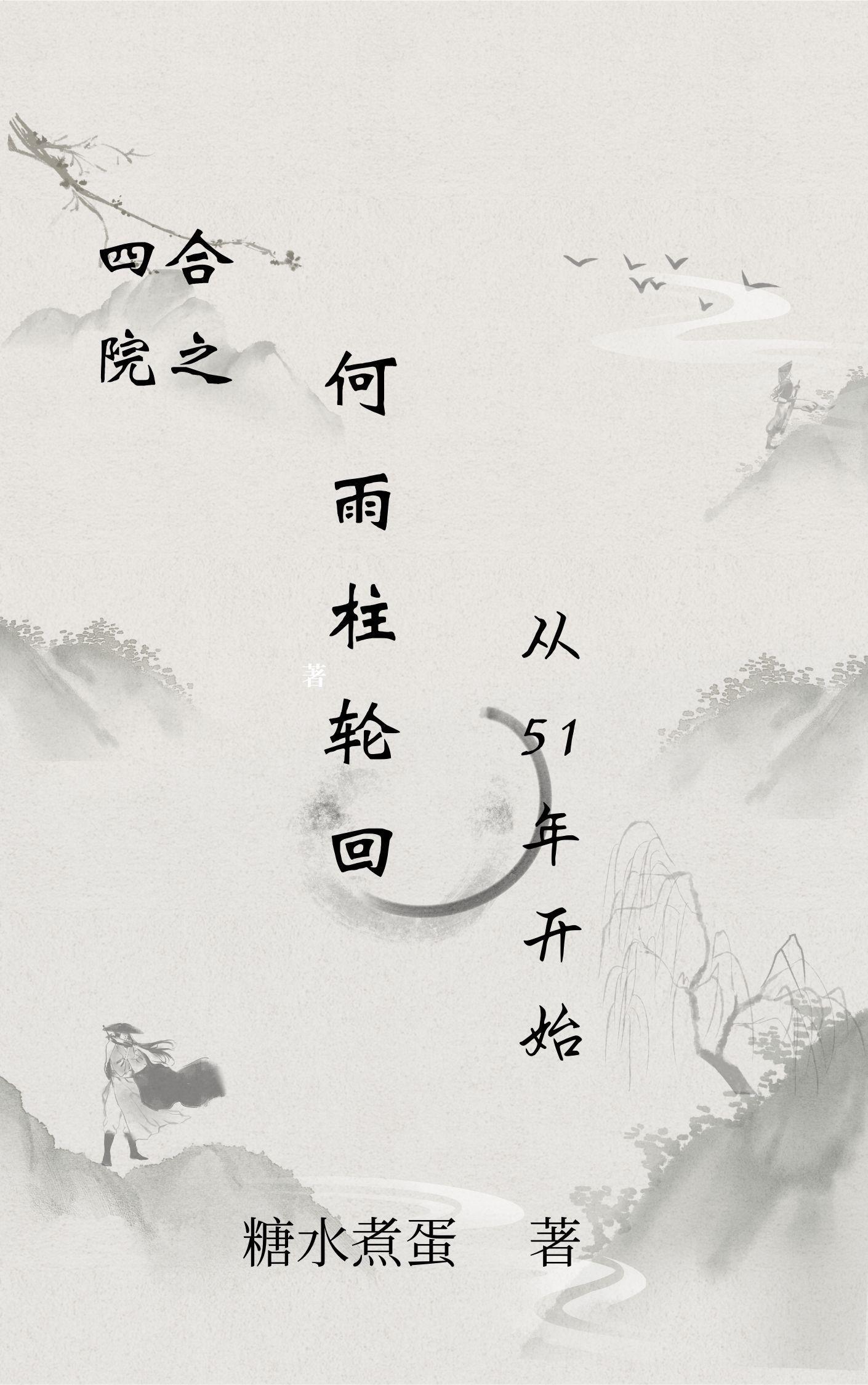爱上中文>素裹银装和素裹银妆的区别 > 第六章(第4页)
第六章(第4页)
“是呀,是呀,您能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虞士臻也迎合着端起酒盅一口喝下,然后乘着还清醒赶紧向自己的话题上带:“李大人,您应该是京城衙门派来滦州供职的吧,学生不才,敢问总工是何头衔哪?”
“我只是总理衙门矿务铁路总局特聘的工程师,没有官衔,只有官俸。”
“噢,大人从东北来,那一定在旗啰?”
虞士臻跟着问。
“不,我是汉人,祖籍锦州,打小父母病故,四岁那年被卖到了水原,继父是朝鲜皮货商人,待我象亲儿子一样,后来考上了汉城工程学校,毕业后就到了南满铁路机务段工作。京奉铁路通车后管理混乱,出了几次事故,朝廷急着选人,俸禄优厚,经朋友推荐我就过来了。”
李源吉像报户口一样叙述了自己的简历。
一听李源吉的如此身世,虞士臻顿时心里觉得有了些谱,赶忙拉近关系说:“哎哟,这么说来咱俩一样的苦命哇,都是打小没爹没娘的孤儿,苦命人。”
李源吉并没有接士臻的话茬,而是转而对大坎儿说:“记得恩兄说起过您也曾在东北闯荡,敢问做何生意呀?”
一提起东北,大坎儿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兴奋地说:“在镖局当镖头,当年咱在南满北满一带那是一路平趟,那年头只要把咱吴大坎儿的镖旗一竖,白山黑土的道上就没人敢拦过。”
“哦?!恩兄走过镖,那一定是一身好功夫喽?”
李源吉饶有兴致地问。
“老喽,不中用了,不过三四个大小伙子不一定能近的了咱的身。”
大坎儿示意石头给三人又倒上酒,然后又端起酒盅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咱兄弟有缘。来,一起再走一个。”
俗话说杯酒下肚三分友。酒过三巡,仨人兄一句弟一句的话都多起来。大坎儿心里挂念着给士臻谋职的事,让石头又斟满酒后就直截了当地冲着李源吉说:“李大人,吴某再敬您三个酒,斗胆求您个事儿,不知能不能给这个面子。”
“这话说的,恩兄就是不敬这酒,只要我能力所及,也一定相帮。这么的吧,咱兄弟俩好事成双,我再回敬您三个,六六大顺。我看呀,虞兄也别闲着,咱兄弟三人就一块端吧,兄弟们凑个九九圆满。”
说着,李源吉把仨人酒盅凑到了一起。
“好,是条汉子,爽快。”
大坎儿回头一把夺过了石头手里的酒壶,给三个酒盅斟满酒。仨人各喝了三盅酒后,士臻就已面似猪肝两眼直了。大坎儿看了眼士臻的醉相乐着对李源吉说:“看看我这个兄弟,蔫不拉及儿地就是个诚实厚道,书读了不少可连个家都养不起。李大人呀,吴某求您的事就是为了我这个兄弟,能在车站上给他找口饭吃不?”
李源吉眼睛一怔,顿了一下对大坎儿说:“我初来乍到,在站上只负责技术,虽和站长一起共事,但人事财务等其他事务基本没有参与过。不过——,既然恩兄开口,我一定想想办法。不知虞先生对职位和薪酬有啥要求。”
大坎儿看了一眼呆呆戳在桌前的士臻说:“唉,读书都给读傻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能有个写写算算的活就中啦。薪酬不薪酬的,他那个私塾一年也挣不了三瓜俩枣的,您能给个糊口钱儿就中。”
李源吉低头思索了一下然后说:“这么的吧,我手下倒是也缺个文书,先从我的薪水里拿出些,让虞先生在我那儿帮把手,赶方便时我再正式给他在站上谋个事。”
“那感情好啦。”
大坎儿乐得一拍大脚站了起来,端着酒盅激动地说:“您真是咱的贵人,俺大坎儿真知不道该咋儿谢您啦,来,我自个把这杯干了。”
等士臻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大嫂盛了碗细棒碴儿粥端到了炕桌上,头还昏沉沉的士臻一边喝粥一边问起昨晚的情形。大嫂把石头怎么把他给架回来,他怎么吐得一身一炕一塌糊涂,石头走前还留下“李大人给他在车站谋了个事儿,要他三天后到车站报到”
的话,一古脑地向士臻叙述了一遍。一听到“车站谋了事儿”
,士臻噌地蹦下炕,一边提着鞋一边对慌张大嫂说:“快,快去学堂,跟学生们就说我今天肚子疼上不了课,让他们放学回家。”
刚一说完又一拍脑门,“咳,瞧我这记性!”
然后,飞了似的向私塾学堂赶去。
学堂里夏剑卿正在给学生们上着课,虞士臻把剑卿叫到屋外,一股脑地把昨晚和李源吉吃饭和李答应他到站上的事告诉给他。夏剑卿听后非常高兴,说马上向上级报告,并嘱咐士臻尽快到车站工作,先静下心好好干,多打听些消息,随时听候上级的指令,瞅时机再做下一步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