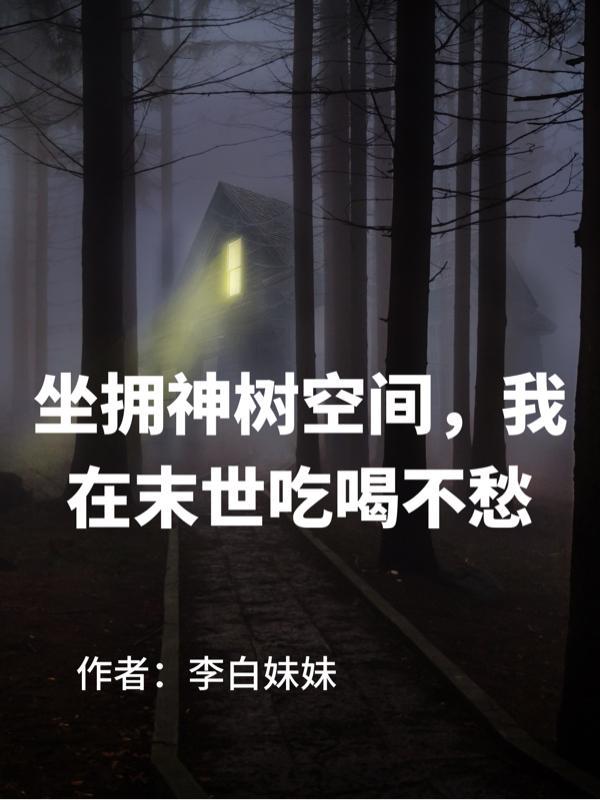爱上中文>烽火之下免费阅读笔趣阁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古来征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防敌对暗动手脚,战时辎重更是重中之重。何况连年战火,大梁开国之际高祖便曾下令对辎重另取一套十分严格的运输流程,又岂会任由老弱妇孺假借成行?
谢元贞与萧权奇相距不过半步,萧权奇一时语塞,便不由打量起这张年轻的脸。他们兄弟二人一左一右,两相对比之下分明是谢元照更貌似其父。只是谢元照血气方刚冲动易怒,反倒是谢元贞沉静内敛更得谢泓神韵,尤其是方才一字一句笃定的神态。
萧权奇自觉有趣,随即冷笑道:“小人瞧四公子还未及冠,怎的这般巧言令色?”
“纵使他们潜形谲迹深居简出,倾六营之力掘地三尺也难说得很!”
谢元贞却不再理会他,只顺着方才的话兀自说下去:“且大军开拔日行不过百里,即便五部不等你的音讯立时发兵,疾行五十里尚且需要半日。劳师袭远非所闻,待五部大军临城,巨石金汁狼牙拍数管齐下,攻城又岂是一日之计?萧权奇,你策马入都不过两三个时辰,若家父以洛都府尹的名义立即将你的罪行公诸于世——”
“两个时辰,”
谢元照摸着腰间佩剑,眼中闪过冽冽寒光,冷哼道:“不,一个时辰之内,萧氏余孽便替你这狗贼先行去探黄泉路!”
萧权奇抬眸神色一凛。
微末的变化之于谢泓无处可藏,随即他指尖一点,与两人视线交错,终于开口道:“立刻着人去寻,边境苦寒,想来萧伯长定思念家中妻儿久矣!”
父子三人一来一回至于此刻,萧权奇终于彻底变了脸色:“这便是世人口中的高门显贵!方才我竟说错了,这天下早不是慕容氏的天下了——朔北、关中、黔西、崤东、岭南,如今该是你们这些世家大族的囊中物啊!可你们累世公卿,把持朝政多年,便该视我们这些寒门庶子为蝼蚁猪狗吗!?”
谢元照听罢怒火中烧,抬腿便是更狠的一脚,“如此便是你投敌卖国,置朔北万民于水火之中的借口么!?高门不与寒庶往来又岂是我谢氏所愿?”
“那又如何!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萧权奇当胸受力,破口笑得血沫横飞,“你们竭力策反,想来正如我所见,那慕容裕夹着尾巴一逃,洛都便再无兵力可言!”
屋内一时只剩下萧权奇的粗喘声。
谈来谈去都绕不开兵力二字,可眼下这两个字便如同悬在洛都头上的闸刀,它无法解救城中百姓于水火,却能清楚地预示这些无辜之人的死期。
良久,谢中书又缓缓开口:“你道我谢氏忝居高位怀银纡紫,今日我便告诉你,我谢氏一门身为大梁子民,是高门也罢是寒庶也罢,无论日后身处何种境地,都决计不做投敌卖国的勾当!洛都有无兵力暂且不论,往南也还有三州方镇军,方才我已修书调兵,五十里,多谢萧伯长肯以实情相告!”
“三州方镇军又如何,你们根本没有见识过翟雉氏真正的实力,”
萧权奇仍在笑,但却已从方才的愤怒转为对于螳臂当车的难以理解,他瞪大双眼,额间的青筋在怒吼中愈加突兀,布满血丝的眸中似乎倒映出半月来九原塞上刻骨铭心的血腥战况,“他们与二十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大梁岂会接连折损精兵悍将!?三州,便是十三州也不过蚍蜉撼树,可笑,真是可笑!”
萧权奇说得对,在场之中唯有束手跪于案前的萧伯长才是大梁与五部血战的亲历者。
谢元照看着他癫狂的模样几番欲言又止:“……他莫不是疯了?”
“三兄,你我心知肚明,他未必是夸大,”
一夜心神激荡,大病初愈的谢元贞脸色更加惨白,此刻他捏着拳头,勉强站直了身,“大军即将兵临城下,我们万万不可轻敌。早年间塞外五部逐水草而居,边境的冲突多因粮食物资而起。后来皇室内斗,结党营私引狼入室是不假,可事关领地归属,物资分配,五部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
他绞尽脑汁,谢元照认同却也不认同:“可时间如此紧迫,又如何令五部自内分而化之?”
“此事确实需要从长计议,不过虽说他们全民皆善骑射,大漠广阔更是战马的优势所在。可兵无常势,我们便是行下下之策,洛都以南便是万斛天关,若保存实力据险以守,静待来日也未尝不可以东山再起。”
谢元贞来回踱着步,手越攥越紧,紧接着又转身回望萧权奇,“只要我们能提前带百姓撤离!”
萧权奇便兀自闭上眼缄默不语。
“「烈士不妄死,所死在忠贞。」1萧伯长,我听闻你曾以一首从军行打动令正芳心,”
谢元贞弯下腰,开口只觉喉间艰涩,血气翻涌:“大兄在家时便常说,行军之人向来以忠信为立身之本。你且扪心自问,今日即便功成名就光耀门楣,就当真是你内心所愿么?”
萧权奇猛然睁开眼看着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一字一顿,反倒越来越坚定:“大梁上品无寒门,说我萧权奇投敌卖国便卖了,我至死无悔!”
“四弟,如此顽固不化的宵小,与他为谋实在是多费口舌!来人——”
萧权奇既打定主意不再透露,再审下去也是徒劳,谢元照便命人将其暂时收押看管,接着扶谢元贞去蒲团边,这才发觉他早已脱力,“你本元未固,快坐下喝口热茶!”
谢元贞自幼孱弱,入冬的一场风寒险之又险,断断续续养了月余才有起色。病去如抽丝,纵于寻常健硕的少年而言也是大损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