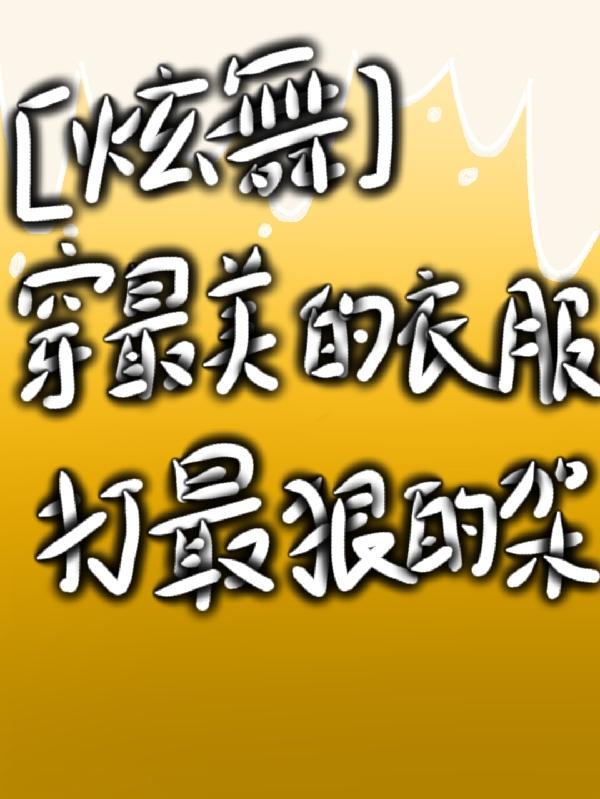爱上中文>红楼宫女 > 第16章 如冰水好四斗百花(第2页)
第16章 如冰水好四斗百花(第2页)
马绾急忙上去半扶半抱着曹颙,泣不成声。在场所有人都跟着低声抽泣。
孙老太君俯下身,轻轻拍着曹颙的背,叹息道:“这职位任免哪里是我们能插得上嘴的?万岁又将江宁织造之职赏赐咱家,已经是对咱家的恩典了,如何还敢再多说话?绾儿,你扶颙儿回去歇息吧,好好养养,过几日还是要进京的啊!百合,你扶你頔二爷回去醒醒酒,让他晚上来上房,家里外面的事,颙儿上京了,还是要他来掌管。桐丫头。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追究了,但是今后,万不可以再自作主张。你去看看太太吧,她这两天好多了,能下地走动了,你顺便把家中这些事告诉她知道才行。”
看着人群6续散去,直到此时,孙老太君才认真地看着若容,想了想,说:“若容,你带我去你们房子,我去看看钰丫头!”
想了想,她问道:“你媳妇病了两年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动不动就心口疼,到底是什么病?傅家为着这个事情,姨太太和傅大爷都来看了多少次,问了多少次了,只差开口质问咱们了。”
若容见问,更加诚惶诚恐:“这……这两年不知道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就是不见效应。她……她也没见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舒服,只是懒懒的,每日歪在床上看看书,或者带着丫头们做针线,只是很少出屋子罢了。”
“你就是这样当丈夫的吗?连你媳妇的病都说不明白?钰丫头是个心思细密,万事明白的孩子,桐丫头这点子手脚,瞒得过多少人,哪件事瞒过了钰丫头的眼睛?她虽然很少出门,都看得一清二楚,要不是她悄悄里告诉我,我都毫不知情呢!你们从小一处长大,你还不明白她?表面冰冷,内心炽热,就算她有千般委屈万般烦难,也绝对不会说一个字,全都自己咽下了,这每日闭门在家,说是养病,其实是心内难过啊!”
孙老太君说着说着,心中酸楚,老泪横流。她的口气忽然变得幽怨:“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颦如已经走了,走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是放不下呢?你这样每日自苦、失魂落魄、虚耗光阴,颦如如果知道,一样也是失望伤心啊!你有那满腔痴情,好好怜惜钰丫头不好吗?!婚后这么多年了,你……你们是夫妻啊!”
若容没想到即使在家计如此艰难的时刻,祖母仍然在顾念他心底那份缠绵难解的情思,居然没有对他一丝一毫的埋怨气愤和说教,不由得跪倒在地,拉着祖母的衣襟,哭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一场。我现在是个废人,自从颦妹妹去了,我的心也死了,什么都没了。我……我也想用心科举、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可是……可是我就算真的做到了,就真的能保住咱家,就真的能应付得了外面的那些人吗?我看得透了看得够了,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我没有那样的勇气!钰姐姐也许能,所以她看不起我,她怨恨我。我知道钰姐姐的委屈,可是她每日经济仕途来对我说教,我……我……我与她在一起,很怕,很压抑,很难受啊!”
孙老太君怜爱地将若容搂在怀里,一如当年,这毕竟是自己最疼爱、最才华横溢、最懂得人心的那个孙儿啊!即便那本书让儿子曹寅气愤失望,但老太君仍然被若容那瑰丽的笔墨和深邃的故事吸引和叹服,“可惜啊,若容,你做个名士真绝代,可怜薄命落名门!这是咱们这样家族孩子的命。你生于斯长于斯,不到大厦倾倒、家业凋零,你都必须要尽最后一丝努力去支撑他!”
孙老太君哭着说。
若容被孙老太君的话感动了,从心里感动了,他低声说:“祖母,我明白了!真的明白了。这次大哥哥上京去,家里的事情,我帮着做些吧!我……我这就回去,回去……好好待钰姐姐。我跟您保证,她的病……她的病,很快就会好的!等她出来与桐嫂子一起主事,您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我……我会的!”
孙老太君带泪地笑了,深深叹了口气,说:“好孩子!难为你了!我……我替颦如谢谢你!我就不过去了。钰丫头好了,让她来给我请安吧!”
若容磕了个头,慢慢起身,转身离去,他听到孙老太君自言自语地说:“今晚不用頔儿过来了,让他慢慢醒酒吧!”
若容苦笑了起来。却原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得意之情只二三啊!他痴心苦守了这么多年,终究,仍是要面对他必须面对的凡尘俗世。若容努力回想着当年这芷园中得子钰,是那样的品格端方,容貌丰美,那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颦妹妹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人生能得妻若此,也当心满意足了吧?
他对自己悄悄念着“不如怜取眼前人”
,认真积攒着心中已将消逝的款款深情,向着阅红轩走去。那里,那个与自己举案齐眉、白头到老的妻子,正在等待着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真实回归。
那颦妹妹,那不过是天上的仙女,不食人间烟火。他忽然心底生出一个怪怪的念头,不知道那深宫中的熙妃娘娘,是不是原本也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降落人间不得已才幻化成了千年妖姬?
这千年妖姬,必然能坦然面对那深深宫院中一次次的艰辛困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