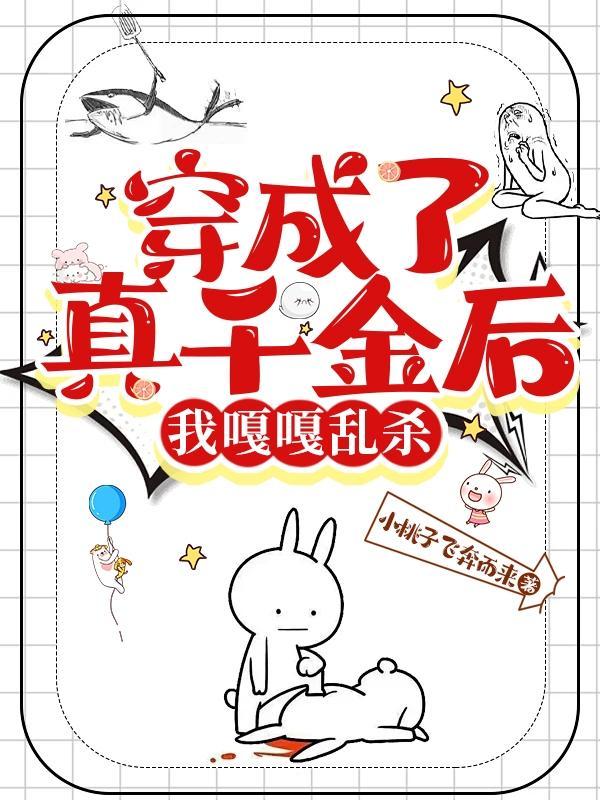爱上中文>女人的衣柜 435 > 先婚后爱宇宙历险记六(第1页)
先婚后爱宇宙历险记六(第1页)
……
凭恕想甩开她的手,他其实力量和技巧远比平树要强,在做杀手这些年也难逢敌手,凭恕以为自己能轻而易举甩开她的手,却没想到宫理纤细的手腕毫不费力一样握着他的手臂。
凭恕咬牙挣扎,她就像是钢铁机械臂,他在她手掌之下纹丝不能动。凭恕目光有些震惊的看着她,他吞咽一下口水,感觉到了某种威胁与不妙,停止了动作。
宫理却歪了歪头。
他在平树体内的时候就注意到过,她饶有兴趣的时候就会做这种歪头的动作。
果然,宫理将脸凑上来一些,看着他的眼睛:“你到底叫什么,你一直没跟我说过呢。”
凭恕挣扎了一下胳膊道:“你松开我,我就告诉你。”
宫理松开手,他甩了甩手臂,半晌道:“凭恕。也就发音一样,字不一样!”
凭恕撇了一下嘴角,觉得自己很有气势的名字应该解释一下,但他说起来莫名没有底气:“……凭什么的凭,饶恕的恕。”
宫理长长的“哦”
了一声,又笑起来:“凭恕,很有意思。不是名字,是你很有意思。既不识相,总会做一些没有用的挣扎;但又在关键时刻知道服软保命,但眼睛里总是闪着那种不会真的认输的……贼光。”
凭恕立刻反唇相讥:“你说谁是贼呢?”
宫理伸出手,捏了捏他下巴,不像是挑|逗,更像是观察手里一个盘的爱不释手的摆件。
凭恕条件反射的有些
想避让她的目光。
宫理又笑道:“你好像就是只要不死都还会挣扎的动物,总有力气尖叫、蹬腿,喊到嗓子哑了也不会保留力气。真有趣,要不断治好你,把你关在时间不会流动的空间里,你会不会一直有力气反抗,一直发明新的词来骂人?甚至坚持几百年?”
凭恕看着她,宫理那种像是发现了玩弄的蚁群里最特殊的蚂蚁一般的亢奋表情,让他恐惧到脊背发麻,让他被俯视的后腰发软。
他张了张嘴,什么声音都没发出。
宫理笑起来:“看你,害怕的更石更了呢。”
凭恕呆呆的看着她,最后只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沙哑变调,听起来像是向强者献媚似的喘。
宫理爱不释手的抚摸着捆绑的绳索:“你是永远都不会真的认输,低着头也会琢磨着反击,不停的犯贱又在心里抽自己巴掌的人吧。真有意思。”
凭恕从她眼里,竟然读到了一丝喜爱。
明明他心里是一直想要跟她密切接触,甚至是总想着偷偷亲她的,她对他的喜爱,应该是一种类似“两情相悦”
的感觉。
但凭恕却在她浓情的目光下,头晕目眩且手脚冰冷。
而平树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心里堵得厉害。
平树隐隐后悔,就在他想要主动终结这种沉默,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重新跟她搭话时,宫理的肩膀忽然挤过来,将脸探过来,非要瞧他的面容。
平树挤不过她,眼睛朝她脸上看了一
眼。
宫理立刻凑得更近:“为什么生气?就因为让凭恕摸了,没有让你摸吗?可你们不是用着同一双手吗?”
她说着,抓住他手指:“那我让你也摸摸。”
平树感觉手都已经碰到她裙摆,他吓了一跳:“才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有要摸——”
他吓得跟快要跳起来的仓鼠似的,宫理果然笑起来。
平树被她拽的不行,他连忙道:“我不生气了!”
“真的?”
“真的!别拽我了,我手指疼。”
他这样说,宫理就松开了手指,她很高兴似的笑眯了眼睛,又凑上来轻轻啄了他两下。
平树本来还觉得自己能再冷一冷脸,但宫理凑上来没完没了的亲他,他没过多久就忍不住亲了回去。
只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总有现实回来提醒他。
几天后,平树在食堂发现自己的饭卡用不了,并且被“老师”
告知要去某个办公室重新激活饭卡时,他就知道自己要见那位“处长”
了。
果不其然,老师一路领着他进入了一道窄门,又是上次一样漫长漆黑的甬道,以及甬道尽头的小房间和桌后坐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