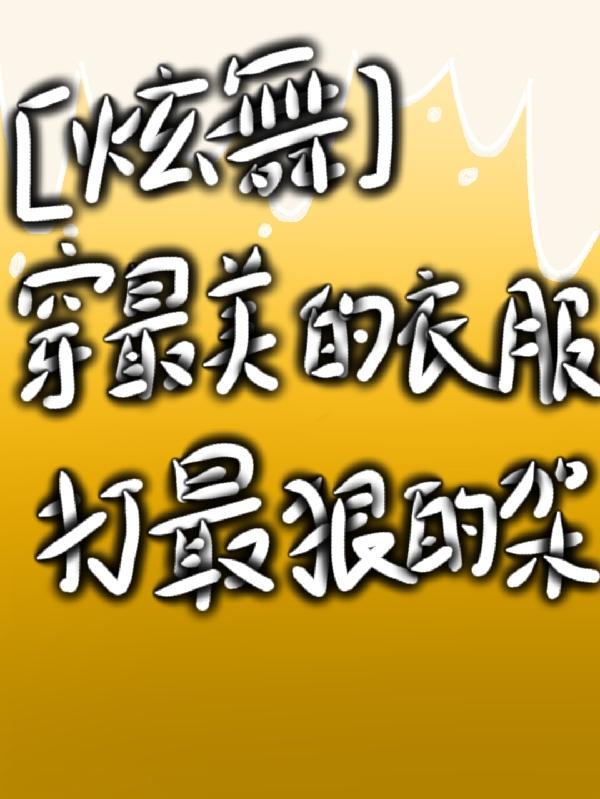爱上中文>鱼目混珠是指什么生肖 > 第56章(第2页)
第56章(第2页)
傅至景抬起头来,他眼睛像是被酒气给醺红了,“你看着我,我是傅至景。”
孟渔感觉到他有很多话要说,眼里承载了年岁沉淀下来的万种情绪,可等了一会儿,傅至景只是再给他倒了酒。
一壶酒很快就分着喝到了底,酒液打湿喜服。
傅至景擒住孟渔的唇,辗转碾压,孟渔躲不掉,被打横抱到龙凤喜被上,一头浓密的黑水似的流下来。
芙蓉暖帐,温香软玉在怀,傅至景无所不有,为什么眼里有泪呢?
为了不让孟渔看着他,他吹灭了蜡烛,圈着孟渔的身躯低喃,“今夜我不是蒋文玄,也不是衡国的君主,孟渔,我很想你……”
他捧住孟渔的脸,“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不高兴。”
孟渔像是听不明白他的一番剖白,在黑夜里睁着水润的眼,半晌才小声说:“我没有不高兴。”
一听就知道是为了讨好他的言不由衷。
“你有。”
傅至景咬牙,迸出几分酸意,“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气我把你从林明环身边抢走。”
孟渔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地又要提起明环,为了截住傅至景接下来的话,只好凑上去堵住傅至景的嘴。
傅至景怔了一下,像是很开心他的主动,反客为主,掀了他的锦袍丢到地上。
孟渔虽喝了不少酒,但脑子还算清醒,清晰地感受到傅至景是如何触碰他、抚摸他,像粘腻的蛇缠满他的四肢,逃不掉,躲不开,只能尽力地顺从才能在这场夹杂着太多情绪的床事里得到几分畅快。
云雨交融,鱼水之欢纵然能带来一时的愉悦,却填不满内心的空虚。
孟渔累得睡着了,懒懒地靠在傅至景怀里,后者望着他微微蹙起的两道眉头,怎么抚都抚不平。
半晌,傅至景低语,“其实那年我没有醉。”
是他情不自禁,先行引诱了懵懂的孟渔。
-
册封礼过后,一切尘埃落地,仿若归于平静,傅至景不再阻挠孟渔在宫中行走。
孟渔外出的次数并不多,时常坐在二楼的宫阁望着远处呆,连伺候左右的宫人都看出少君的郁郁寡欢,变着法子讨他开怀,木偶人、投壶、皮影戏,什么有趣的玩意儿都送到他跟前,可惜收效甚微。
倒是一个不起眼的花灯得了少君的喜欢,挂在殿里,时常要去观赏一番。
他还是每日巳时放风筝,纸团里的话只有他和蒋文慎知晓,他告诉蒋文慎,见风筝如见人,要王爷好好治疗双腿,等何时能不依仗轮木椅行走那日他自然会去相见。
蒋文慎的腿要恢复如初俨然不可能,但有了太医院的医治,能在阴寒天气减少些疼痛。
今日天气不错,孟渔难得地打起精神到外头闲逛。
居然遇到了正在放风筝的蒋嘉彦,很是不得要领,迟迟放不上去,又不让宫人帮忙,气得跺脚说不玩了。
孟渔忍俊不禁,走过去捡起他丢下的风筝,牵着线小跑了一段,风筝成功地飞到天上去。
蒋嘉彦哼道:“有什么了不起的。”
孟渔逗他,“那你学我做什么?”
“谁学你了?”
蒋嘉彦气结,“我随便玩玩而已。”
孟渔笑着把线棒交给他,蒋嘉彦瞅着他,“谁要你……”
被敲了一脑壳,“别装腔作势了小殿下,给你就拿着。”
他走到旁边找了块石头坐下,两只手杵着下颌看蒋嘉彦玩乐。
两个恰好来修建花木的小内监朝他行礼,低声说着话,“东南门那个洞还没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