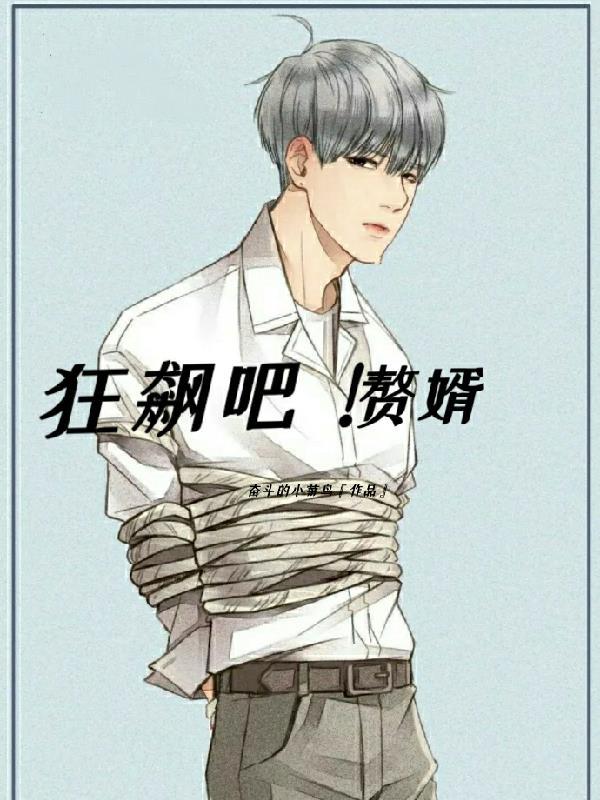爱上中文>落火全文免费阅读在线阅读无弹窗 > 第98章(第2页)
第98章(第2页)
白鹤庭的耳朵也被那把火烧着了,抬手环上了他的腰。
“早就同你讲过。”
可沙哑的声线让白将军的训斥失了严厉,“在战场上,不要三心二意的。”
骆从野的喉咙骤然一紧——
一只手顺着他的后腰,一寸一寸地往上。他用右手捞住白鹤庭的背,正欲将人抱起,那只手却停了下来。
白鹤庭突然问:“这是入冬的时候伤的?”
骆从野在诧异中抬起头。
白鹤庭的手指正按在他的肩胛骨之下。在那个位置,有一处刚愈合没多久的箭伤。
那一箭距他的心脏约有三指距离,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也害他休养了将近十日。他当时千叮咛万嘱咐——谁都不许把他受伤的事传回岛上。连林在常与林浅都被蒙在鼓里。
“谁通风报信的?”
他不爽道。
白鹤庭的手指在那处陌生的伤疤上停留片刻,把手抽出了来。
“那周的信,”
他平静且简短地答,“很短。”
骆从野呆了呆。
“怎——”
白鹤庭话没说完,身体猛地失去了重心。他条件反射地搂紧骆从野的脖子,无处安放的双腿在空中晃了几下。
但骆从野抱他抱得很稳。
他用双手托住白鹤庭,面对面抱着他往前走。白鹤庭这才放松了一点,手指下滑,按了按那硬实的背肌。
去前线历练了一遭,这家伙比以前更结实了。
似乎还长高了。
白鹤庭少见地羡慕起alpha来。十八岁那年,他的身高已经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同龄人。可分化成oga之后,骨骼仿佛停止了发育,几乎没有长过个子。
这个曾经只有他一半高的小鬼,如今竟高出他这么多。
“抑制贴,帮我撕了。”
骆从野被他摸得呼吸愈急,脚下的步子也迈得大了。
这话的语气有些刺耳,白鹤庭低头看他问:“又命令我?”
一丝愠怒爬上那紧拧的眉头,骆从野把他往高颠了颠,诚恳地向他解释:“我腾不出手。”
说完,又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很眷恋地蹭了蹭。
“憋好久了。”
他的嗓音也软了下来,听起来闷闷的,“难受。”
--------------------
我真服了。不能在这里修文,一修就进审核。
床帷在匆忙间只拉了一半,不同于在都城时的克制又小心,也不同于重逢后的强势又无礼,今日的骆从野似乎与往常都不太一样。
白鹤庭在混乱的脑袋里搜刮了一个尽可能贴切的形容词。
缠人。
他推住骆从野的肩膀,歪头躲开一点,哑声道:“别亲了。”
半遮半掩的帷幔泻出浑浊火光,白鹤庭的皮肤却白得透亮,那雪白之上又浮起一层浅粉。骆从野吻掉他唇上的水光,又去吻他浅淡的眉毛,眼下的泪痣,挺翘的鼻尖,最后吻回那双淡红的薄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