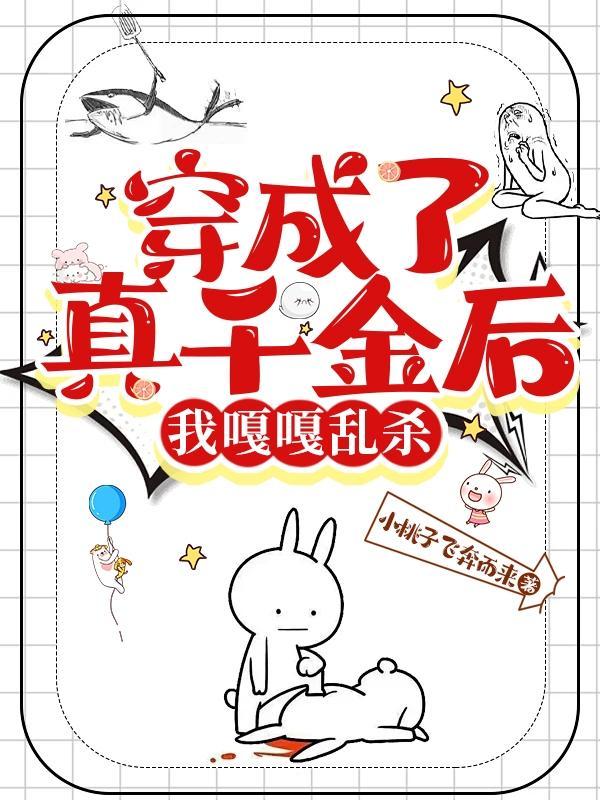爱上中文>海澜之家女人的衣柜不缺字完整版 > 想象(第1页)
想象(第1页)
……
宫理觉得,或许是她和平树太没有学术基础。
她只有感觉,却并不能触摸到任何理论与规则。
也或许是那根尖刺与触角,从虚空之中探过来,只是拨动的力场涟漪波及了她和平树,它实际是轻微地点过这十个人的头脑,像水黾在湖面上滑行而过一样……
其他学者仍然沉浸在那种清醒的喜悦之中。
周春去紧紧握着笔,他的双眸像是扫过无数诗行一样快速左右颤动着。那位女学者像是被扼住喉咙般,欢呼似的道:“光速在另一套法则中也没有被超越,至少我们的时间是安全的!那套数学法则应该跟我们同处一个维度!”
却也有人剧烈地摇起头来,不赞同她的想法。似乎他们大脑,像是晨光熹微中冰凉的草叶,正有智慧的露珠在凝结,每个人的动作都变得幅度更大,还有很多人仍然跌坐在地上满脸懵懂,整个大厅看起来都像是幼儿园的课堂。
他们没有争论,都在小小的呼吸着,宫理扫向高处的时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强撑着,坐在了凳子上,另一只手在外套中紧握着打火机冰冷的外壳,静静望着那些学者们。他们或仰头看向天花板,或低头喃喃自语,这一生最甜蜜的时刻,最煎熬的凌迟,正在他们身上交汇。
另一个世界的数学法则在极小范围的几个人头脑中的降临,像是
巧合,像是被迫求生,它们绝不是彰显力量与不同,更不是任何威慑或恐惧——
它们更像是旅行者号上搭载的那张金盘。
迷惘地望着同样边界不明的夜空,来做了一场混乱的自我介绍。
平树没有坐下,他一只手搭在宫理肩膀上,他们俩就像是朋友聚会里的两个尴尬的局外人,一站一坐许久说不上话来。
平树忽然开口道:“那个尖刺在缓缓往回缩了。”
她们有种从冷水里被捞出来的喘|息感,她所能感受到的一切,都从身上流淌下去回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大海,她身上连最后一点湿痕都即将消失。
时间已经只剩下三四分钟了。
大厅没有任何窗口,只有一扇被封锁的大门。但宫理早就感受到了外面隐约传来的多人脚步,他们一定已经包围这里了。
宫理也看到,那些学者面上显现出了失落与巨大的空虚,那智慧终究像是即将被晒干的露珠,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
周春去松开铅笔,手在空气中挥舞了两下,像是要抓住什么:“不!不要——”
他们才对那个世界的奇妙数学从皮毛了解到内里,一切就要消失,他们想拼命用自己的大脑留住知识,留住感觉。有人想要奋笔疾书,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有人甚至大喊着,却发现只能说出两个世界的共性。
就要这样了吗?
00:02:57。大厅内的时间还在倒数。
他们的生命恐怕也
只剩下三分钟——以及无尽的失落!
周春去忽然踉跄地朝大厅的混凝土金属液压门冲了过去。
宫理知道,时间到达之前这门从内还是从外都不可能打开的,他也不是要去用清癯的身子去撞门,而是冲向了门边唯一一个跟外界能沟通的通话器。
平树:“他要做——”
宫理却一瞬间理解了,她猛地站起身来,却不是要阻止,只是感觉心脏剧烈收缩起来。
周春去手按住通话器,对着大厅之外必然早已埋伏的人们开口道:“这个世界不只是一种数——”
砰!砰砰——
他胸口先炸开一团几乎洞穿的血肉,浇在灰色的墙面上,紧接着心脏处的炸|弹会在爆炸的同时顺着脊柱向他大脑弹射另一枚旋转的尖头炸|弹,他的颅骨会在撞击到尖头炸|弹的瞬间将他的大脑彻底引爆!
连续几声密鼓般的爆炸,周春去的整个上半身炸成血色烟花,溅在墙壁与地毯之上。
他不是想要告密。
他是要用死亡留住另一个数学法则走后拖行在他头脑中的湿痕。他不要在巨大的失落中迎来死亡,他想要自己的头脑在最后一刻,仍然保持着两套法则并行的愉悦,那一刻,仿佛他睁开了十六只眼睛看着夜空——
周春去用死亡留住那瞬间的做法,竟然启发了其他人,宫理看到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从工作台后冲下来,冲向那台通话器。
他们都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透
露任何信息给外界,他们也确实不想——只是想要就死在这一刻!
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同时将手拍在了血肉模糊的按钮上,吼道:“他们带来了数学的命……”
00:01:13。
砰!砰砰!砰!
宫理几乎要缓缓闭上眼睛,数团绚烂的血肉炸上天空,溅了后面的学者满头满脸。
甚至有人在周春去的血泊中滑倒了,一时站不起来,她极其惊恐地感觉到自己快要忘记了——忘记两套数学法则是如何嵌套,忘记那些奇妙的矛盾与运行。女学者竟然将求助般的目光看向宫理,一个字都没说,那满脸是血中黑白分明的双眼中只有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