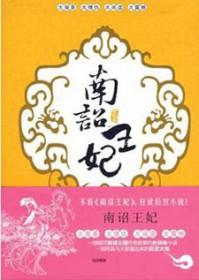爱上中文>熟夜并无别事 七穹烬番外 > 第62页(第1页)
第62页(第1页)
他最擅长忍耐。
--
接下来的几天,盛凌薇自己因病休息,也给团队放了假。
说是要在家休养,其实多数时光都在和沈恩知约会。他们在巴黎的街道闲晃散步,经过衣着松弛的人们,穿行在拱门和里巷尽头,触摸廊柱上竖直的凹纹,在转角咖啡厅倾斜的蓬顶下面暂躲太阳。
巴黎的色彩总掺一点灰调,在晌午骄阳之下也不饱和。象牙黄的墙体,雕刻着奥斯曼建筑独有的古典肌理。深釉红的店招街牌,窗格栅栏雾蓝暗绿,均是雅致而神秘的大块纯色。
在塞纳河畔一条缀满鹅卵石的碎道上,沈恩知悄悄问她:“能不能牵一下手?”
盛凌薇朝他一瞥,评价:“装模作样。”
不光拉起手,还勾下他的脖子要亲。
沈恩知脸上是清汤白水的神态,以掌心挡她的下颌,一本正经说:“不可以,薇薇。你说过的,我们要从头开始,慢慢来……”
“怎么慢,我说了算。”
她几乎是不讲道理的,张牙舞爪把他的手挪开,垫脚吻上淡红的嘴唇。
他们有几次去贺思承的店里。巴黎好玩的夜店不多,贺思承这家新场更是是个中翘楚,环境氛围和音乐品味俱佳,整体调性前卫,无可挑剔。
贺思承专门留了几天的中型包间给他们,自己除了在楼下迎来送往,也会提着酒上来。有时是珍藏的红酒,陈酿烧白,或者几打啤酒。
见面次数多了,贺思承自觉和两人熟络起来,恢复以往玩玩闹闹的模样,对着她手指上明晃晃的钻戒打趣,在桌沿连着敲开五瓶科罗娜,笑嘻嘻说几克拉就要喝几瓶。
沈恩知也不扫兴,只说她胃不好,自己替她挡。
沈恩知的酒量深不可测。这几天和贺思承胡饮下来,盛凌薇还没见他醉过。
回到公寓,他怕酒精刺激到她的胃,喝了果汁和清水才来吻她。
眼底和呼吸之间仍有醉气,他用力地往下亲,把她抱得好紧。
连续几天腻在一起,最多亲密到唇面擦碰的地步,仿佛重温一次单纯青涩的初恋。肢体保持了距离,两颗心却渐渐在走近。是以沈恩知回国之后,盛凌薇重新投入工作,每天都拉着他远程通话,有时方便就打去视频。
盛凌薇总是讲许多话,描述生活工作中每一处角落,而他安静专注地听。
沈恩知一般不会主动打扰她,每日等着她结束工作后的来电。有一天盛凌薇正在装扮,忽然接到他的视频邀请。她心下未免奇怪,暂时请退了化妆师和助理,接起来问:
“国内现在不是午夜么?怎么还不睡。”
沈恩知见她素净着一张脸,不知想到了什么,指尖迷失地触在屏幕上,眼神也稀少地敞露一丝惘然:“突然醒了。薇薇,你要嫁给我了……就是想确认一下,我不是在做梦。”
盛凌薇笑了,轻轻说:“你不是在做梦。”
他也跟着笑:“那么要谢谢你。你不知道那天在海边给你套上戒指,我觉得有多幸运。”
盛凌薇“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