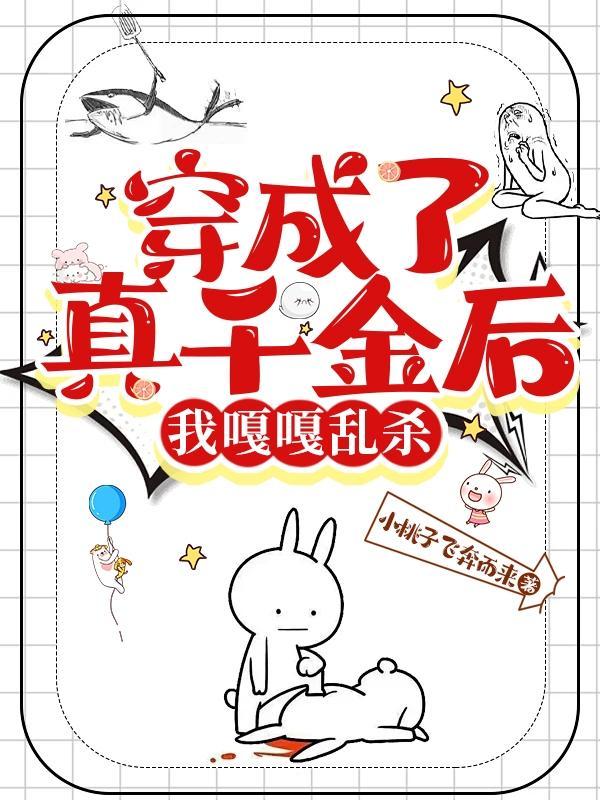爱上中文>飞蛾扑火真的会被烧死吗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我交了一个历史专业的朋友,她问我想不想出去走走。就这样她成为我的旅伴。以曼彻斯特为轴点,我们去了利物浦,谢菲尔德,普雷斯顿,利兹,布拉德福德。我们循着工业革命的足迹探寻这个国家。但走过的地方越多,我心中的念头越发强烈。
我要去伦敦。
周五没有课,下周一有节课,我只需要在下周一五点前赶回去就好。在冲动的驱使下,我定下最近一班去伦敦的火车票,没有约我那位旅伴。这并非旅行,而是为了寻找什么。
这是我一个人的旅途。
在酒店放下行李,我来到皇家音乐学院,沿着仅存在记忆里的街区,我去了她家。伦敦变化不大——或者说,一成不变。想要找到某个记忆中的地点很容易。我知道在那之后大伯父原本想将房子全权委托给伦敦的房产经纪人,大伯母阻拦,二人吵了一架,最终还是将房子闲置了。
只因那房子,有她曾活过的证据。
窗帘紧紧拉着,一丝缝隙也没有,不给妄图窥探的人留一点余地。像是住在这房子里的人暂时离开了,马上将要回来。我站在街边,像是一个跟踪者,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等待,等待着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人拉开窗帘。
天快黑了。我回到酒店。仅凭借一腔热血来到伦敦,到了这里却漫无目的。我计划了四天的行程,第一天已经过完,我还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能再这样下去。我粗略规划了一下,明天大英博物馆、福尔摩斯博物馆,后天南肯辛顿的几家博物馆,v≈ap;a、科学博物馆与自然史博物馆,周一国家美术馆。
而后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她曾带我走过的路线。原本她并没有计划福尔摩斯博物馆,是我想去贝克街221b,临时更改的行程。她总是将计划做得很详细,甚至精确到在哪个展厅逛多久。她像个时钟,不停歇、不失误的时钟。我曾以为时钟永远不会停止。
世界一如既往,一如时钟还在运转。
只是我的时钟从在那时就停止了。
当我走进自然史博物馆的大厅时,我的心脏随着视线而停滞。人海川流全都消失,只剩我和空旷的大厅,空旷的大厅中央没有任何东西。
它不见了。
以那样熟悉的方式,再一次消失在我生命里。
取而代之的,是一具悬挂在大厅中央的雌蓝鲸骨架,名为“希望”
。
希望啊,可是你从不曾降临。
我失魂落魄地离开博物馆,一路上遇见的热心路人,问我还好吗。
当然,我很好。谢谢你。
——对啊,我很好。
但为什么,我的内心却爬满了不可言说的痛楚,就像蛛网一样,纤细,一触即破,密密麻麻地织绕在我的心脏外层将它裹挟?
你存在过,你存在的痕迹却随着时光流逝被一一抹除,时间抹杀掉所有铭记你的证人证言。最终,你被取而代之,被忘记。然后,你真正死去了,就像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那样。
不!
我记得你,我追赶你,我成为你。
我们一同死去。
今天伦敦下大雪,已经好多好多年没下到这种程度的大雪,你看到了吗?
自然博物馆前面的冰场,小孩推着企鹅趔趔趄趄往前挪动。花滑是我唯一能超过姜砚秋的爱好。每次回国她都要我带她去滑冰。后来我一松手她就摔得特别惨,我找教练帮刷脸去借了海豚。她说自然博物馆门口的冰场超级美,以后要带我来这里滑冰。
我来了,你呢?
即使明知不可能,但我也抱着一丝幻想,姜砚秋会从大街的另一头跑来对我说:“不好意思迟到啦,我刚刚去买奶茶了,这是你的。”
我说,我不喜欢喝甜的。她说生活已经那么苦了,偶尔来点甜的也没有关系。她总以为英国奶茶全糖和中国奶茶全糖是同一个概念。一个是奶茶里加糖,一个是糖里加奶茶。结局是必然是那两杯奶茶喝了两口就都丢了。冬天天黑得快,而我捧着那两杯全糖奶茶已经由温热变得冰冷,天也黑了。她没有出现。
姜砚秋,我恨你。
我真的好恨你。
天上突然落下雪花,不是一片片飘下来,更像是一团团砸下来那样,毫不吝啬将人间洗净铅华,仿佛是为了重生的洗礼。
我不知为何突然开始奔跑,朝着雪落下相反的方向奔跑。路人皱眉地看着我,又冷漠地转回去。
我是他们一年到头见到不知道多少个怪人之后的又一个怪人。
我在摄政公园站的站台,碰见了另一个怪人。
两个怪人如同磁极一样相互吸引。
在伦敦风雪交加的夜。
原来是你。
可我自始至终,真相都缄默于口。
关于那个她已不在的真相。
或许留一点念想,对她,对我,对姜砚秋的父母。
有人因着那一点点念想而活。
就此别过。
我又转身,目送她的背影消融于白茫茫一片中。
——“untilweetaga”
…
——有朝一日,希望你能与她再次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