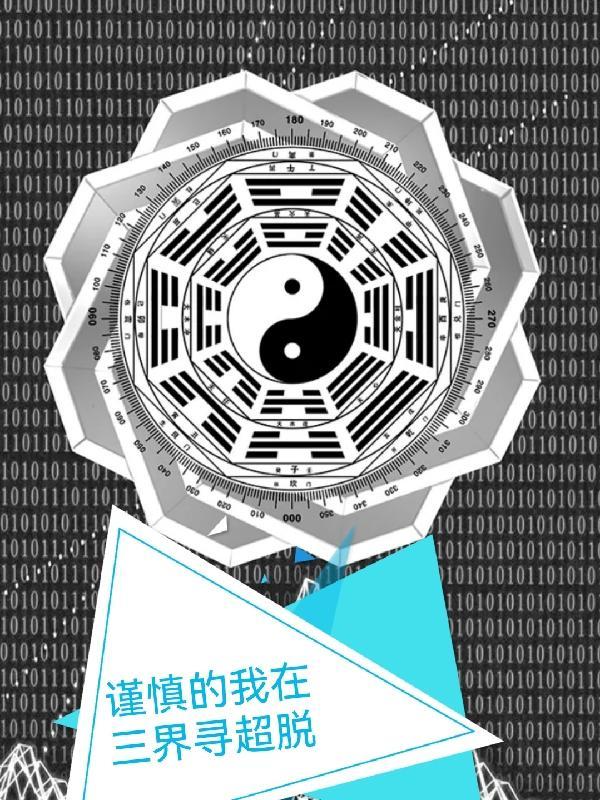爱上中文>如风二十载讲了什么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我们这类人,天生是会被你这类人吸引的,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向日葵天生是要追随太阳的,大雁天生是要追逐南方的,我们这类人,终其一生,都是会发疯一般寻觅你这样的人的……”
“如果找不到,就会变本加厉地去寻找。如果找到,那就是毁灭,带着甜蜜的毁灭。”
他停顿了更久。
你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看清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像犯了热病一样发亮发热,他的重庆口音像山城的大雾一般将你包裹。
“我怕你什么……?”
苏锦华低低地笑了一下,“顾如风,我怕你的一切,你走路的样子,你吃饭的样子,你认真听课的样子,你睡觉的样子,你……无时无刻不在勾引我,我说了,我们这类人,天生是会被你吸引的……”
你沉声打断他:“够了,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他浑身一颤,放软了声音:“不说那些了。顾如风,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送你一样没人看见的礼物好不好?”
他跪在你面前,用无比虔诚的语气说:“我想取悦你,用尽我的一切取悦你。我想匍匐在你脚边,任你差遣,我愿粉身碎骨来换取你的愉悦……”
他俯下身,他埋下头。
你震惊地睁大了眼睛,咬紧了牙关,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放开。”
他变本加厉。
你坐起身,抓住他的肩膀,再次警告道:“放开。”
他的声音里带上了破碎的哭腔,因嘴里含着东西而含糊不清:“求求你,让我这么做,我忍了太久了……”
明明是你最脆弱的地方被他钳制,他的声音却绝望得好像他自己被捏住了脖颈。
你完全冷静了下来,一手捏住他的喉咙,一手扬起,精准无误地扇在他的脸上。
啪的一声,宿舍里只剩急切的呼吸。
你冷冷地说:“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和禽兽有什么区别。从我身上滚下去。”
这个当口你竟然还有空去想,许潇然告诉了你男生和男生可以谈恋爱,而现在苏锦华却让你知道,男生竟然还能对男生有欲望。
真是荒唐。
他跪在你面前,脊背弯曲,你在黑暗中俯视着他,微微发麻的手掌撑着床垫。
在急促的呼吸声中,他拉过你的右手覆在他滚烫的嘴唇上,他像一只不知道该拿主人怎么办的小狗,亲昵地蹭着你的掌心,灼热的气息经由手腕钻入睡衣的衣袖。
“疼吗?”
手心的灼烧让你恶寒,他声音里的亲昵讨好更是让你震惊。你反手又给了他一巴掌。
“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你说,“滚下去。”
你率先下了床,去卫生间冲冷水澡。寒冬一月的水彻骨的凉,却恰好能浇熄你内心的愤怒与震惊。你打了好几次沐浴露,把皮肤搓得发红甚至破皮,才堪堪洗去被毒蛇缠住的黏腻不适触感。
宿舍夜晚是断电的,从阳台到床位都是黑暗。洗完澡的你从卫生间出来,熟视无睹地路过书桌旁的人影,踩着爬梯换下了床单、被罩和枕巾,抱去阳台开始洗。
银白的月光下,你的手浸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搓洗着床单。
脚步声跟在你身后,停下,惴惴不安的声音响起:“顾如风……”
“别和我说话。”
你打断他。
身后静默了一会儿,他的脚步声远去,离开了宿舍。
你洗得很慢,似乎在享受刺骨冻肉的凉意。等床单洗完晾好,你的思绪终于回归身体,你平静了下来。
离去的苏锦华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像等待枪决的犯人一般神魂不定地靠墙站立,他迎着你走了两步又顿住,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你,声音忐忑:“别冻着手了,抱着暖暖。”
递过来的是他去热水房灌的水杯。
冻得失去知觉的手骤然接触到热源,有一瞬甚至变得更凉,重重地刺痛起来。你把水杯放到书桌上,从衣柜里拿出备用的床单铺好,这才打开充电式台灯,宿舍顿时亮了起来。
苏锦华紧张地站在一边,看了你一眼后立刻心虚地低下头,他左脸上顶着鲜明的巴掌印,微微肿了起来。
你拉过椅子坐下:“发完酒疯了?坐。”
他在你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却僵硬地只坐了一个角,似乎只要等着你一声令下,就准备跪地求饶。
“‘你们这类人’,这个词组你说了许多遍,指的是什么人?”
他说:“就是……我们这类人。天生就知道自己会臣服于另一个男人的……这类人。”
你又问:“我这类人,在你刚才的语境里,又指的是什么。”
不知是不是为了缓解紧张,苏锦华竟然短促地笑了一下。
“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竟然真的不知道……”
他说,“这么久了,你没注意过么?每天课间操时间,隔壁班龚成的目光从头到尾都黏在你身上,一秒都舍不得移开。还有我们班上的蔡俊,你以为他天天站在楼下的成绩红榜前看什么?不就是看你的照片吗?晚上你去操场跑步,和你装作偶遇的小白脸能数满一只手吧。你竟然全都不知道。”
你平静地开口:“这些都是你的臆想。别东拉西扯,请回答我的问题。”
他低低地笑了起来:“顾如风,你不懂。我们这类人身上天生装有雷达,一眼就能甄别同类,他们都是我的同类。你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磁铁的另一极,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吸引力。”
你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的意思是,你是见到大粪的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