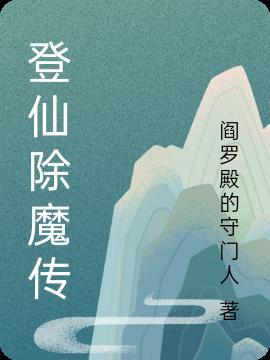爱上中文>岁事当长贺全文免费阅读 > 第50章(第3页)
第50章(第3页)
范震昱一哽,“我什么行事风格?我就不能为民请命,秉公办案一回吗?”
“您向来,修身养性,志在无为。”
班贺说得委婉。
“以前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县丞、典史能处理,又何必我费心?”
范震昱说得理直气壮,话音落下,却神色黯淡下来,露出委屈的表情。
他长叹一声,道:“龚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是元光十二年举人,等了三年才有机会上任。当了七年知县,历经四个县城,一个比一个贫瘠,才知道什么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知县。每每稍有起色,就会被调离,到了玉成县,还是如此,你叫我如何能甘心?”
班贺问道:“不是任期三年一满,经过吏部考核,便有望升迁吗?”
范震昱:“官缺只有那么多,哪儿能人人都升迁?龚先生,我范某人虽不是什么爱民如子的好官,可我自问尚存几分良心,绝对做得到清正廉洁,又哪儿有钱去上下打点?”
地方官员对京中官员,下属对上级,送礼各有名目,冰敬碳敬,三节两寿,这些是常例,都是官员们薪俸外的收入。下属不贪污克扣,哪来的供奉?不能给予供奉的下属,谁又愿意去提拔?
一个萝卜一个坑,既然范震昱不能归顺,那便不能让党羽之外的人占了位置,这才是范震昱会落得如今下场的真相。官员上任,需要吏部批核委任,吏科给事中签字,怎么可能临时冒出个马大人。
话说到此处,班贺已然明白,这件事从头至尾都不可能是单纯的事故,而是一场被隐形的手操纵的棋盘。范震昱、钱炳、谢缘客、还有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冤魂、被驱逐的无助伤者,都是操纵者侵吞的棋子。
范震昱不敢直说,班贺却明白,眼中只有盐利的官老爷们,找不到处置他的理由,那就随便制造一个罪名,让他来担这个办事不力的责。
为此不惜害死人命,不惜酿成如此大的灾祸。
抓着衣服的手死死掐紧,班贺痛苦地闭上双眼:“怎么能……怎么能这样视无辜人的命如草芥!”
躺在病榻之上的谢缘客,现在还处在危险中,不知大夫医治情况如何了。马大人下令驱逐那些伤者,目的极有可能是为了尽早清理现场,恢复盐井生产,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强行出手。
此刻身在阱室,若是强行出去,那他的身份就成了逃犯,班贺毫无查案的权力,被动地陷入两难境地。
班贺将脱身之事暂时放到一边,仔细询问:“范大人,你说你要彻查案件,可是有什么线索?”
“这个还真有!”
范震昱坐直了,“死伤者的身份我都派人清点核查了,谢缘客倒在离盐井最近的位置,而离他最近的人,却与盐井无关,不是做工的工匠,更不是煮盐工坊的人。钱炳认出他来,不过是村里一个游手好闲的混子。”
班贺表情紧绷:“那人现在还活着吗?”
范震昱摇摇头:“我进来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昏迷不醒。现在,那就不得而知了。”
班贺心一沉,如果那人就是纵火的罪魁祸,会不会被指使者杀人灭口,谁也说不准……
第7o章火井
当务之急,是要找人确认那名为潘二的伤者安危,若是还活着,必须保住他的性命。不知谢缘客何时能清醒,火灾生的那晚,到底生了什么,这两人最为关键,绝不能出事。
班贺心中忧思郁结,几乎凝实在胸口,沉甸甸地压着他。几日来奔波劳累,快马加鞭赶来,未进水米,此刻再也坚持不住,双眼一闭,倒了下去。
正说着话,范震昱没料到他就这么倒了,整个儿一弹,趴在栏杆间,极力往间隙里挤:“龚先生,龚先生?你这是怎么了?还能听见我说话吗?”
短暂的昏厥很快退去,班贺小臂支撑着身体,四肢冷无力,心悸紊乱,想对范震昱说一句无事,都无力张口。
“来人啊!”
范震昱冲着门口大喊,“快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