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文>陶渊明读山海经孟下草木长 > 第20章(第2页)
第20章(第2页)
真奇特,连环的案件也会让他变得多疑敏感。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做什么都不能单凭直觉,正如再厉害的渔夫也不能单凭鱼叉得到大马哈鱼。
可他硬是在身旁这位精致如珠宝的外表下,看出利刃出鞘般的冷硬。
“谢谢你的伞。”
道尔回过神来时,克里斯蒂已将样刊卷成卷儿塞在大衣里,“希望下次见的时候是好天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卷烟叼着,瞥了道尔一眼,淹没于迷雾之中。
三、
“第八个了。”
阿道夫将卷宗递给道尔。他近日雪茄抽得格外勤快。
“女人?”
“没错,26岁。”
阿道夫道,“这一回刀口不一样,是横切。而且前几次都是尖刀,这一回似乎是匕首他拿走了子宫。”
道尔对他的烟瘾表示不可容忍,于是退避三舍。
“死者死在酒馆客房,门是反锁的,几乎是密室杀人。墙上”
阿道夫塞给他一张冲洗过的照片,“你自己看吧。我们发现一块带有死者血迹的抹布,上面有刀刃挑过的痕迹。”
照片冲洗得不算成功,但道尔还是看到了墙上暗沉的印记。
是一张扭曲的、淌着血的笑脸。
“珍妮丝说,这样的人有性经历方面的创伤或者心理变态”
“我想你们太过于把关注点放在凶手个人身上了。”
道尔将照片扔在一旁的木桌上,“明天,最晚明天,我要八个死者的全部资料。”
这个二十六岁的漂亮女人他见过,在东城区的玛格丽特酒吧,离白教堂很近。道尔的助手艾伯特是那里的常客,他们在那里喝过一杯。
说是酒吧,其实是个满是嫖客的春楼。法国人的淫靡粉脂气在板正的道尔看来,像伦敦暗处的毒瘤。
“你最近去玛格丽特了没?”
回了事务所,他脱下风衣时问艾伯特。
艾伯特轻咳一声,说了句“se-curitaiscarsa(为了保险)”
,又补上一句:“我那医生说,我这个月去都容易留种。”
“被杀的女人,你遇到过吗?”
“索菲亚·杜勒沃。”
艾伯特推着眼镜,“她价位太高,不怎么干净。凶手没准是她那几个情人——这类案件多了去了。”
“开膛手是她的情人?”
没有回应。他们再次陷入一个逻辑怪圈,无用地揣测开膛手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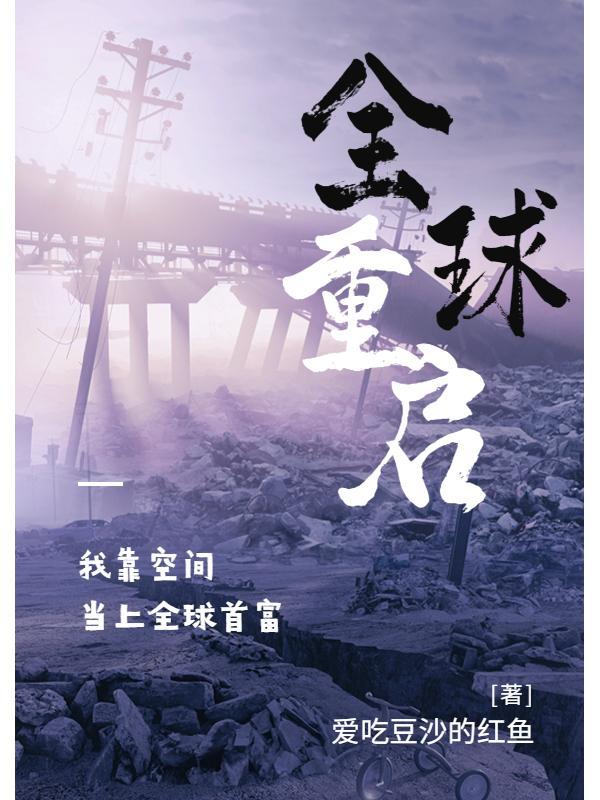
![被迷恋的劣质品[快穿]](/img/1403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