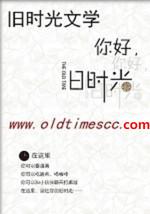爱上中文>罗伯特麦基将故事主题划分为 > PART 2 人物创作(第3页)
PART 2 人物创作(第3页)
“如何将自己投射进一个与你本质对立的人的潜意识中,凭的是胆大妄为的天赋。”
——亨利·詹姆斯[1]
灵感的第二
大源泉是将作者置于其人物宇宙的内心,而不是她自己的宇宙的中心。一个富有探险精神的作家会将自己的想象触角直探人物的内在自我,用人物的眼睛去观察,用人物的耳朵去倾听,感知人物所感知的一切,以此来激活自己的创作。她想象人物的冲突,模拟人物的选择,对人物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亦步亦趋,就好比人物的虚构生活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这种从一个意识向另一个意识的跳跃,如亨利·詹姆斯所指出,靠的是特定的天赋。我将这一技巧称为“人物内写作”
。
当“人物内”
作家寄居于角色的内在自我后,她的情感就成了人物的情感,她的脉搏会跟着人物的脉搏一起跳动,她的愤怒会在人物的心中燃烧;她会庆祝人物的胜利,爱人物之所爱。当作家经历着人物的经历时,最最强大的灵感便会油然而生。换言之,人物的第一个扮演者就是作家本人。
作者就是一个即兴演员。她首先会把自己想象进人物意识的最中心。一旦开启“人物内”
模式,她的思想、情感和能量便能驱动人物创作。她在地板上踱步,手舞足蹈,念念有词,演绎着她的创作成果——男人、女人、孩子、怪兽。作家就像演员一样,生活在人物的感官之中,对故事事件耳闻目睹,就好像她本人就是人物的活化身一样,于是乎,发生在人物身上的
一切也发生在她自己身上。
作家如何才能开启“人物内”
模式?她如何才能即兴演绎她所创作的人物?她如何才能利用她自己的情感来给一个虚构生灵注入生命力?此时此刻,她还得再一次召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魔术般的如果”
。
在给人物注入生命的努力中,作家可以自问:“如果我处于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
这一想法肯定能让她思如泉涌,但作家毕竟不是人物本身,所以,作家在那一刻有可能说的和做的,也许根本就不像是人物将要采取的行动。
或者作家可以自问:“如果我的人物处于这种情况,我的人物会怎么做?”
不过,这一想法就是让作家坐到了观众席上,就好比是从观众席上为台上的人物画像。如此一来,作家在此时此刻并不是在感人物之所感,而是在猜测其情感,而猜测则几乎永远是陈词滥调。
因此,为了启动“人物内”
模式,作家必须按照这样的想法来运用“魔术般的如果”
:“如果我是这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做?”
换言之,作家必须演绎这个场景,但并不是演她自己,而是要演人物。现在,作家的情感便开始流动,但不是作为她自己的情感,而是作为她的人物的情感。
“人物内写作”
的意思,远远不只是思考人物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是意味着生活于人物的内心,于是乎,你的
大脑占据了她的大脑,她的自知变成了你的自知,你们俩成为步调一致的一体。掌握了这种“从内到外”
的技巧,就能把人物写活,无论在纸上、舞台,还是银幕,其真实感和微妙性是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能达成的。
这种灵感只有在一个虚构人物的内心深处才能找到,想要发现它,就得凭借持续的、恣意的,常常是勇敢的想象。拥有这一才艺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对自己的内在生活的有力洞察。你对自己的真实本性越了解,你对你的人物的复杂性的认识就会越深刻。为了了解你自己,你必须能够识别你最底层的内在自我,将你的各种梦想与现实进行比对,把你的各种欲望用道德进行衡量,并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各种社会的、个人的、私密的和隐藏的自我,来拼合你的多面人性。你的真相将会变成你所创作的每一个人物的真相。
所以,在你企图尝试“人物内”
技巧之前,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一个人类个体多层面的复杂性。
观察者和被观察者
大脑由大概1000亿个神经元构成,并交织着100万亿个神经末梢与外界互联。如此超越想象的庞杂系统在与身体互动时会时时刻刻进行调整和改变,然后再通过身体与周围的物理世界和社会环境进行互动。每过一天,大脑都会进化出新的思想、新的情感,然后将其储存于记忆,以备未来
之用。
不知为何(尚待科学来发现到底为何),意识会超越并跳脱于这个庞大的一致性系统,不仅知道其周遭的事物,还具备自知功能——能退居自己身后,将自己视为一个客体。[2]
对内在自我的本质,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争执不休。它到底是一个现实存在,还是一种幻觉臆想?一个凝视着自己的头脑,所看见的自己到底是一种真实自我,还是一个反射无穷现实的镜像?
即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佛家相信自我是虚幻的,因为我们头脑中一切的缘起,都仅仅是从我们头脑外部的像与声所感觉到的视听印象而已。我们称为自我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束依次出现的外部痕迹而已,就像一个进出舞台的演员一样。因此,真实自我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无我”
(anatta),一种精神特效。
苏格拉底颠覆了这一点。他相信,人类不仅有一个坚实的内在场域,而且其中还住着两个自我: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核心自我(观察者)是意识的中心,它观察着生命的流逝并试图理解它。核心自我将代理自我(被观察者)派到外部世界去采取行动。核心自我于是便能感知到行动中的代理自我并变成了它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观众。这便是自知之明——是你正在上演的内在戏剧,但这出戏无人捧场,只有你在看。[3]
考虑一下这个情况,在
你做了某件傻事之后,你是不是常常会想:“你个白痴!”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到底是谁在骂谁呢?当你终于获得了一项成功之后,你常常会想:“我做对了!”
是谁在拍谁的后背?自我批评和自我恭维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谁在跟谁说话?
当你在读这些文字时,你内心深处的一种观察知觉便一直在追随着你的每一个步骤。你先是察觉(看着你自己阅读),然后是行动(在纸上做笔记或将其储存于记忆)。脑海深处的这种“从知觉到行动再到知觉”
的旋转运动便将核心自我与代理自我分割开来。[4]
不过,直到今天,还是有一些神经科学家依然站在佛教一边。他们认为,由于大脑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单独的功能,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区域本身会导致自知,所以,一个核心自我是不存在的。[5]
其他人则赞同苏格拉底:人类有马达神经元负责动作,有感觉神经元负责感官,还有中间神经元——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面二者——负责思想的举重运动。由于有过去经历的残留和对未来事件的想象,大脑便能与身体的神经系统以及瞬时发生的所有感官遭遇进行对接,将亿万个冲动聚焦于意识的中心,即核心自我。因此,自知便是所有的神经元同心协力地在所有这些区域进行工作的一个副产品。这便是大脑任何一个区
域的损伤将会减损甚至摧毁自我意识的原因。自知的高峰体验,即观察与行动,只有通过一个健康身体的营养丰富的大脑才可能辐射出来。[6]
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埃及人早就将这一“观察自我”
视为一个保护精灵,并将其命名为“身魂”
note"
sr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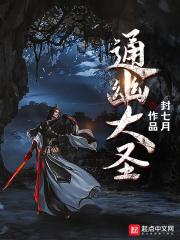
![[演艺圈]死灰不复燃](/img/23372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