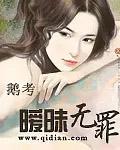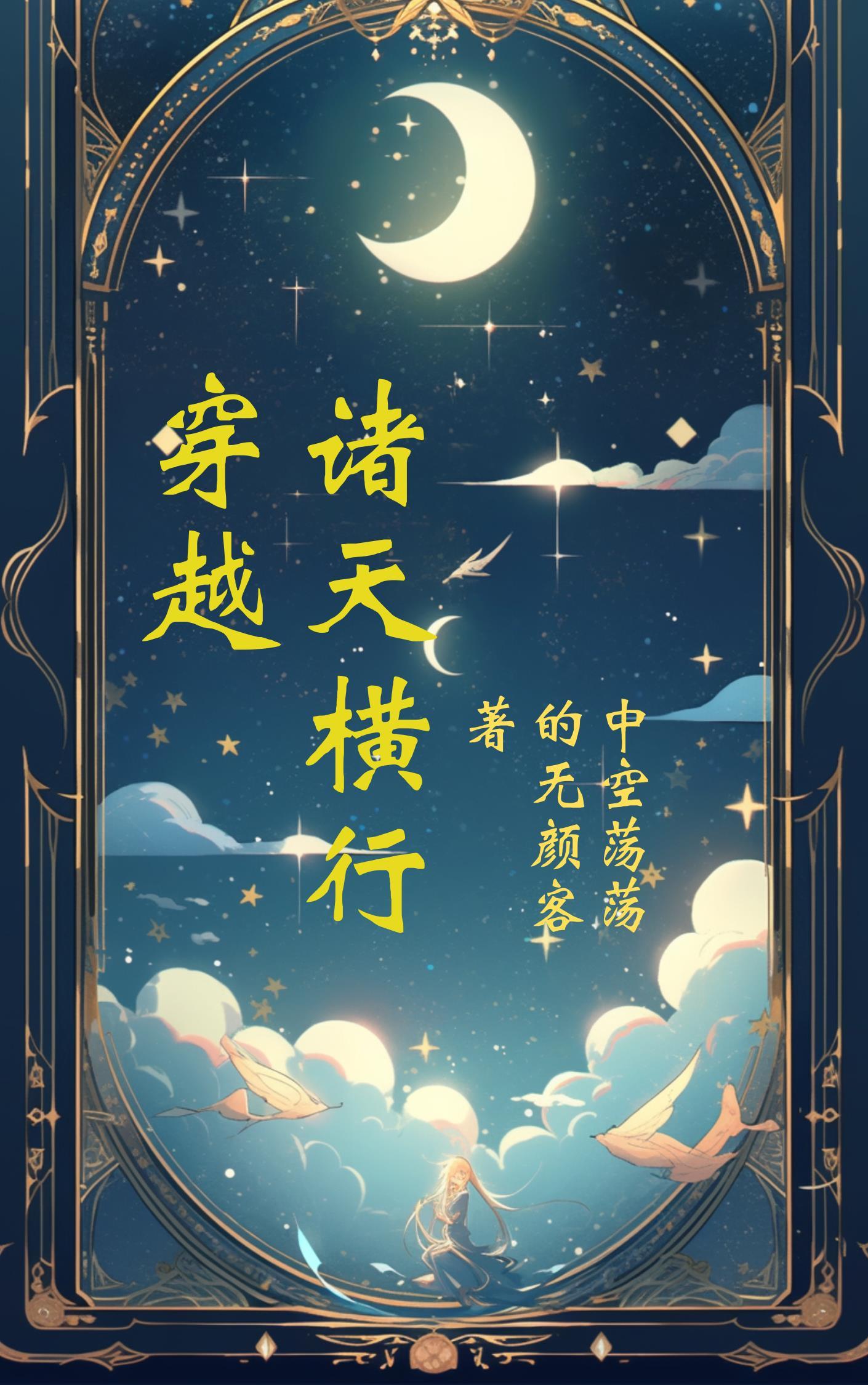爱上中文>罗伯特麦基将故事主题划分为 > 译后记(第2页)
译后记(第2页)
和“隐藏自我”
四个层面,提出了“四个自我寻找一个人物”
的概念,用以彰显复杂人物的各种维度,辅之以各种独具一格的图表与图示,犹如精确的GPS,生动形象地引领作家
读者在“人物宇宙”
中开疆拓土,发明创造。
《故事》《对白》和《人物》,虽跨度二十余年,但作为“虚构艺术三部曲”
,三本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堪称一个完美整体。而《人物》作为其“完美句号”
的独到之处在于,即使你没读过《故事》和《对白》,它也能自成一体,将故事元素和原理作为不可或缺的有益背景融会贯通于人物建构的探索之中。而且,从“三部曲”
的副标题便能窥知,其读者面是层层递进的:《故事》主要是面向专业编剧,即银幕剧作家;《对白》则扩展到了“文本”
和“舞台”
;《人物》则更具普适价值,因为它几乎就是一部关于“人性”
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艺学等领域的具有可读性和娱乐性的科普著作。只要是对“人性”
这个永恒命题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阅读趣味。哪怕是无心成为专业写手的业外读者,也能对书中的条分缕析叹为观止并感同身受,并对自己这辈子在各种文艺作品中已经邂逅和将要涉猎的各种伟大的“虚构人物”
有更加直观生动和细致入微的认识。
书中的每一章每一节,都凝聚着作者对这一行当的挚爱与激情,其特有的率真、渊博与睿智透射于字里行间。读之便能深受感染与激励,促使自己更加努力,成为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成功、更加真诚的专
业作家。正如作者在序中阐述的,“人物不是人。人物之不是人,恰如《米罗的维纳斯》《惠斯勒的母亲》和《甜美的佐治亚·布朗》之不是女人。人物是一个艺术品——是对人性的一个深情的、有意味的、值得纪念的比喻,它出生于作者的心智子宫,安卧于故事的怀抱,注定要得永生”
,愿咱们的读者都能得益于本书,学而时习之,反复捧读,创造出这种“安卧于故事的怀抱”
的“注定要得永生”
的“不是人”
的艺术精品。
多年来,有很多朋友说,《故事》,尤其是老版并无太多译注的《故事》,看了很多遍都没真正看明白,那是因为罗伯特·麦基所独创的一些故事概念,如“激励事件”
“人物弧光”
等,中文读者因为文化差异而始终难得其正解。所以在这次《人物》的翻译过程中,还是秉持果麦版《故事》的原则,尽量加注,尤其是涉及文化差异和产业理念差异的地方,都会加上译注。
同时,为便于读者更好地读透字里行间的潜文本,麦基先生自己也在书尾加了名词解释,对核心概念进行了属于他自己的阐释。
比如,在中文语境中闻所未闻、被统称为“配角”
的“支持型角色”
和“服务型角色”
,作者便特意在“名词解释”
中给了明确界定:
支持型角色(SuppRole):一个人物,能够促进场景
但不能影响事件进程。
服务型角色(ServiceRole):一个人物,其行动能够影响故事事件的进程。
再如在《故事》中首次进入中文语境的“激励事件”
,在本书中,也给予了充分阐发,并同时出现在名词解释中:
激励事件(IngI):一个故事线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激励事件就是指“以冲击力开始的事件”
。这个事件会彻底地颠覆生活的平衡,并激发出主人公的超级目标——力图恢复平衡的欲望。
另有一些不同于咱们的传统表述的概念,尽管我已经在正文中加了译注,还是觉得有必要在此厘清,以免读者产生阅读障碍,比如:
另外,就像《故事》一样,本人在翻译的时候,尽量提升文本的文学性,因为原文风格还是像《故事》一样,是脱胎于讲义的。而作为一个文论,本身的文学性应该也是默认值,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尽量在这个属性上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提升和美化。好比刘勰的《文心雕龙》,如开篇的“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其本身的文学性应该已达到文论之最高境界。即使撇开其理论性不谈,其作为文论的文学性亦能令人叹为观止。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的翻译原则是,必须“用中文来说英
文”
,让读者读到地地道道的中文,而不是“用英文说中文”
,以至满纸翻译腔,尤其要用文学的中文来传译那些不太文学甚至并不文学的英文,因为它是像《文心雕龙》一样的文论。这便是我一直在“中国电影走出去”
的理论与实践中反复强调并在拙著《号脉电影》(增订版)中进行了深入阐发的“文化变译”
论:好比“器官移植”
,必须首先从文本上杜绝“排异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