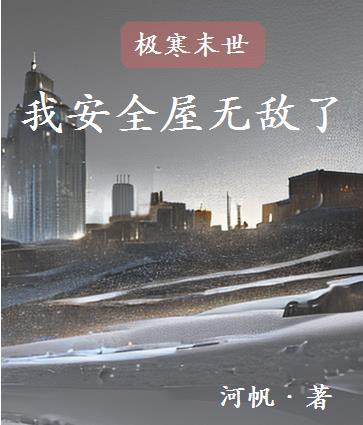爱上中文>纨绔休妻记垂拱元年 > 第46章(第1页)
第46章(第1页)
雪香还在气着夏氏饭席上对自家姑娘平白无故的一番教训,瞧了瞧四周无人,关上门抱怨道:“那曹姬是侯夫人她爹还是她娘啊,侯夫人对她那么好,姑娘您生病都没见侯夫人叫人送东西来!”
罗婉自然清楚夏氏用意,厚此而薄彼,防合而谋我,宗越这厢妻妾相争,获利的是夏氏和她那双儿子。
她无意为难曹姬,只要她不冒犯她,不挑拨宗越,她不会容不下她。
···
宴春阁内,曹姬望着漆木匣里的红枣,手中攥着一个小玉瓶,犹豫不决。
小玉瓶里装的是油煎水银,乃避孕神效之物,医家言服下如枣大一枚,不伤身子还可断绝孕产之忧,胡玉楼的女子多用此物避孕。
若少服些,该无碍于日后受孕的吧?
曹姬倒出红豆大小的一枚,放进去核枣的空心里,填进口中几乎没怎么咀嚼就咽了下去。
又拿出二十余个去核枣,挨个放入豆子大小的油煎水银,放置片刻待那药物粘着牢固,才又混入没放药的枣中。为着排查方便,她特意抓出十来个枣放在盘中作平常食用状,里头混上四个放了药的枣,余下则仍放进漆木匣里。
做定这事的第二日,曹姬便借口身子不适请了大夫。
消息递到宗越这里时,他正陪着罗婉在千峰翠色阁验看做好的盒册。
“不是请大夫了么,我又不是大夫,禀我作甚?”
宗越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这段日子和蕃商打交道,有些酒局宴席上的应酬需要歌舞伎人助兴,曹姬自告奋勇,他才带她去的,谁知道她风寒未好,这几日又是跳舞又是喝酒,病愈发重了,他强制将人带回,已经替她请了大夫,怎么又来烦他?
“世子,您还是回去看看吧,曹姑娘这次病的不轻。”
宴春阁的小厮乞求道。
宗越皱眉,忖了片刻,还是丢下罗婉,骑马赶回了府中。
一进宴春阁,就见曹姬倚卧榻上,眼睛红肿,显是哭了一场,而葛大夫站在旁边,神色凝重,好像曹姬果然重病似的。
“怎么回事?”
宗越没往曹姬跟前凑,只是看向葛大夫询问。
葛大夫遂将验出药物的红枣递与宗越看,说了事情原委,“曹姑娘说肚子不舒服,但我从脉象上诊不出什么来,问她说是只吃了枣。”
他指了指已经切成两半的几颗红枣,“这几个枣里放了断绝孕育的药物。”
又指指另一盘自匣中挑出的枣,“那些也是。”
宗越知道这枣的来处,是罗婉的随嫁侍婢拂云亲自送过来的,那日来送时,他就在宴春阁。
默了会儿,他才又问葛大夫:“她可有大碍?能治么?”
“这药是用来避子的,不必长期服用,一次就可绝后患,因而一些不欲再生产的女子都会服用,书上言,这药只要不超过枣般大小,于人身体无大碍,我行医多年,确实也不曾遇见过吃这物吃坏身体的,但曹姑娘说肚子痛,脉象上又诊不出什么,不知和这物有没有关系。”
宗越遂又看向曹姬,“你吃了多少?”
那一匣子枣虽没有定数,但大致能看出少的并不多,宗越一向机敏锐利,曹姬不敢在这事上欺瞒他,遂说道:“十来个吧,也没多少。”
就算十来个枣里全都放了药物,剂量应当也够不上一个枣那般大小,何况依现在药物枣的几率,她吃下的应当没那么多。
“你想怎么办?”
宗越看着曹姬问。
她既哭成那样,又特意差人叫他回来,显然就是觉得受了委屈,要让他主持公道。
曹姬愣住,没料想他知道真相后的第一句话是质问她想怎么办,而不是去质问他的嫡妻,为何要给她下这种药。
他果然好喜欢那个罗氏,就算知道罗氏给她下绝孕的药,第一反应也不是去质问责备她。他问她想怎么办,就是想自行解决,息事宁人吧?
她真的想不通,他买她回来做什么,她出身昭武旧城,确实有一身畜养鹰犬的好本事,可他花八百两金,就是为了让她驯养鹰犬么?
她的容貌,她的舞姿,他从来都是看看就罢,以前在胡玉楼,还会逢场作戏地要她斟酒伺候,自从买回家来,他反而对她没了兴趣,但凡她离的近些,他就冷着脸看过来震慑她。
她原来不甘心,不信自己比不过那个罗氏。
但现在,她不甘心也不得不认命,她在他心里,就是比不过罗氏,他都不护着她,真闹大了,这侯府里会有人护着她么?
她连个妾的名份都不曾有,嫡妻就算明目张胆要她绝孕,也是不触犯律法的,更何况现在,她病的不重,连大夫都说无甚大碍。
既动不了罗氏,她又何必自不量力地硬碰硬。
她又落了两滴泪,忙拿帕子抿去,才低低地说:“少夫人不想我有孕在先,本也无可厚非,是我不懂事了,不该惊动世子,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世子放心,我不会和任何人说的。”
宗越想了想,允了她所言,鞶囊里摸出一锭金饼放在案上,算是补偿,又说:“以后我会管着她些。”
说罢,看向葛大夫。
葛大夫忙表态,“我也什么都不会说。”
宗越微颔首,屏退葛大夫,正要离去,听曹姬说道:“世子,您今夜能留在这里么,我这几日总是噩梦惊醒……”
宗越不耐烦,“你我各睡各的,我留下何用?”
见曹姬垂头低泣,想她到底受了委屈,也不知这几日的噩梦和那药有没有关系,遂压制下眉目间的不耐,“行了,我会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