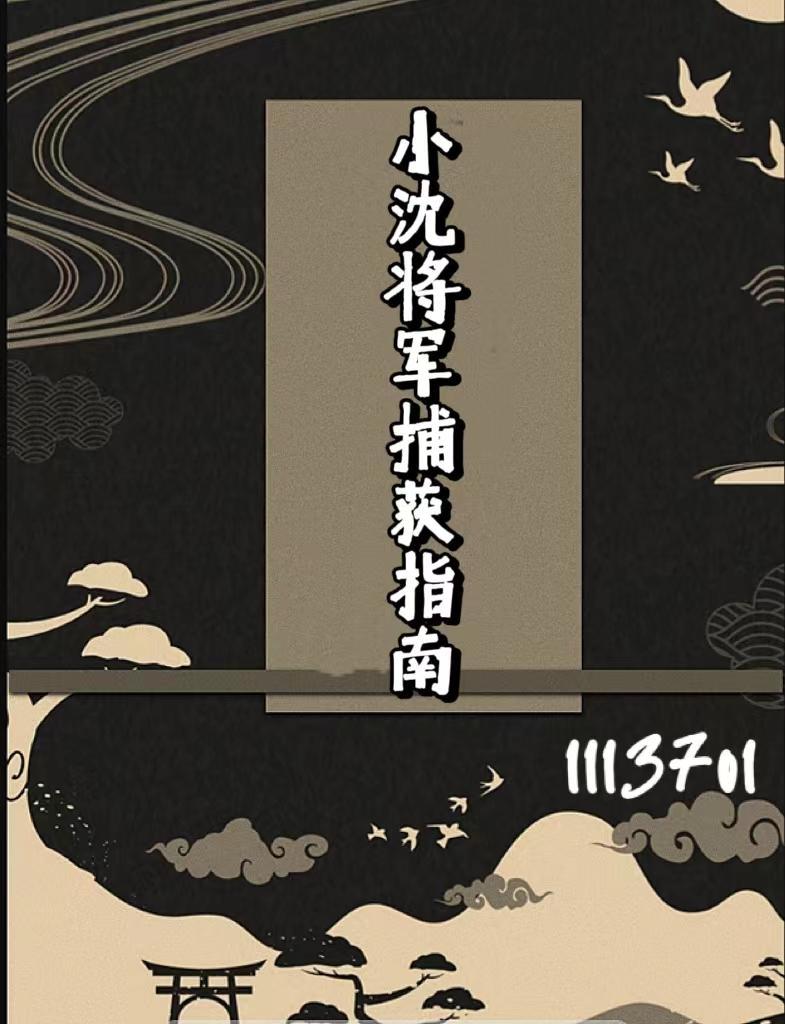爱上中文>青南计划工资大概在多少 > 第63章(第3页)
第63章(第3页)
玄旸赠送青南的那件玉簪,从玉料的质地看竟是块稀罕的西离白玉,白玉无暇,细腻如油脂,材料极难获取,而它的琢玉工艺更是精美绝伦,竹节造型的碧玉簪挺,嵌入西离白玉制作的扇形簪,簪镂空,簪面两端各缀上一枚打磨圆润的绿松石片,造型优雅又肃穆。
这样的器物,往往需要最精湛的玉匠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制成,无论从材质还是工艺看,它都是一件玄夷城不可多得的珍宝,唯有国君及其配偶才能拥有的玉饰。
指腹轻轻摩挲玉簪,青南陷入思绪之中。
麂子在一栋舒适的屋舍里美美睡了一觉,第二日清早才去见青南,青南领他登上郭城城墙,一睹羽邑的全貌。麂子对羽人族的风土与习俗十分好奇,对这样一座宏大且处处呈现出颓败的古城亦表露出惊诧、惋惜之情。
两人登下城楼,沿着荒凉的北区行进,进入莲花怒放的池苑废墟,在一处垮塌的墙体上坐下,借树影庇荫,麂子开始讲述去年夏天生的事情。
“那会老国君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但凡玄夷城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只要老国君去世,玄夷城就得出大事,人们私下议论,心里恐慌不安。
为什么这么说呢?
觋鹭应该听说过玄邴有位异母兄长吧,他叫玄谷,那恶徒母亲是个霁夷人,出身低微。老国君将玄邴立为嗣子,可是玄谷就不是什么善人,他为立嗣的事心里怨恨,暗中与霁夷人勾结。
老国君的身体一直不好,玄邴又贪恋杯中酒,对管理城中事务不上心,渐渐人们就对他生出不满来,尤其他的亲信都是大皋城人,这些大皋城人终日与玄邴饮酒寻乐,平时又十分骄横,都不知道误了多少事,得罪了多少人。
国人就有了想法,觉得玄邴偏心外人,对他更加不满。
玄谷趁机拉拢不少人,想要夺取玄邴的嗣子之位,也是从这时开始,有一伙霁夷人来到玄夷城,被玄谷养在身边,都是些凶狠好斗的恶人。
玄邴也知道国人渐渐厌恶他,他也日益消沉,对什么事都不管不顾。
要是玄旸在,玄邴向来听玄旸的话,还能劝告他几句,可惜我们派人去文邑找玄旸,没找着,只听说文邑王派玄旸出使大鹰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麂子摇了摇头,叹息:“那时要是能将玄旸找回来就好了,也不会生后面的事情。”
青南在一旁静静倾听,没有打断麂子的讲述。
“我记得那日玄邴去探看病重的老国君,出来对我跟几位一起长大的伙伴说,他说:‘老家伙一点也不遵守自己过的誓言,我不能昧着良心,日后叫我的子孙受人讥笑,你们快去将旸哥找回来,玄夷君本来就该他来当!’
玄邴是这样的人,他清楚自己的才能远不如玄旸,也感念玄旸的恩情,一直都不想当嗣子,感到愧疚,可是老国君与国君夫人又硬是逼迫他。
他心里很痛苦,才一直饮酒消愁。
我曾听老巫祝说,当年玄旸的父亲将国君之位让出,我们老国君在祠庙誓,说日后他将立贤不立亲。
如果兄弟之中有贤能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又比不上,他会立兄弟的儿子做嗣子。
按誓言,老国君应该立玄旸做嗣子,国人也都这么认为。
所以玄邴才说老国君违背誓言,又说自己的子孙要受人讥笑。
玄邴遣人去文邑找玄旸,我也想将玄旸找回来,就动身赶往地中。”
麂子稍作停顿,他坐在残垣断壁中,见到勃勃生机,成片怒放的莲花,似乎因这样奇景而走神,或者只是单纯的说累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他的讲述。
“我知道老国君撑不了几天,玄夷城又有传闻说只要老国君一死,霁夷君的军队就将渡过霁水,出兵协助玄谷成为新的玄夷君。
我知道玄邴在玄夷城中失了民心,可也不想看到玄谷当我们的国君,玄谷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在家把他那些妻妾像牲畜一样打骂,对下人更是残酷。
我去文邑的路上就听说文邑出了大事,文邑北境的裕伯叛变,将文邑王的嗣子掠走,后面又听说文邑的军队在北裕与靳人作战,心想这可麻烦了,玄旸肯定不在文邑,还得去北裕找他。
等我到达文邑,又听说文邑王已经杀死裕伯,文邑嗣子也给救回来了,那些靳人挺能打,可也不是玄旸的对手。
正是玄旸亲自率领文邑士兵,将靳人赶出北裕。
我还是来迟了,玄旸不在文邑,也不在北裕,文邑的祁珍跟我说玄旸前些天刚离开,说是要去盘城。
我嘛,没别的本事,就是腿跑得特别快。
我在白湖追上玄旸,告诉他老国君快不行了,是玄邴派我来请他回去,他不肯。”
麂子叹声气,把两条大长腿换个位置摆放,他一只手臂搭在膝盖上,垂着眼,喃喃道:“我就说啊,我说为什么别的地方有难你都帮,你帮高坪人守城,你帮文邑王击败靳人,就对自己人你不管不顾。
我那时特别着急,话说得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