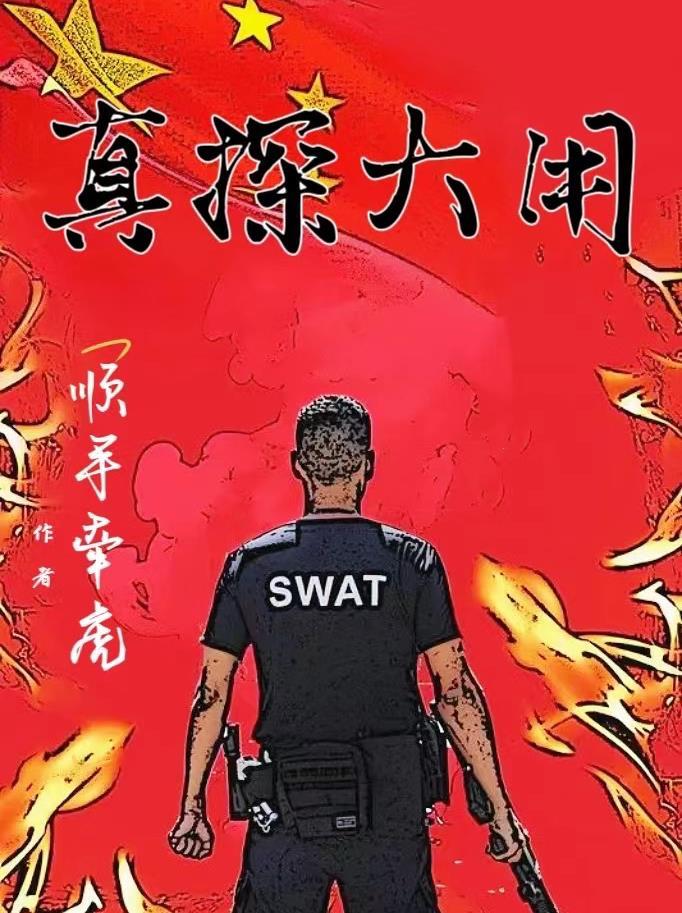爱上中文>贵女只想当权臣全文阅读 > 第39章(第1页)
第39章(第1页)
“昔年新政……”
禾女摇摇头,“是我与族人无知。”
“陶氏先祖曾于襄国立下赫赫战功,我等后世子孙亦得荫蔽,从军可优先论功,耕犁享封地族领。”
“世子却要收回世族一应优待,并与庶野一视同仁。”
时秋往嘴里倒了口酒,喃喃道:“这怎么能行呢?这要是我,也绝不同意。”
禾女仰头,望着雾蒙蒙的夜空:“但假若早这么做,哪还有什么世族叛国,旧襄覆灭呢?”
“宁做强国庶民,不做弱国卿贵,宁做弱国庶民,不做亡国之奴。师姐,你常年隐居山间,恐怕无有体会,国弱则民哀。”
时秋轻摇酒壶:“襄国弱,可靖国强,为什么不愿做靖国的子民?”
“那不是靖国的子民,是靖国的猪狗,他们高兴了赏你一块骨头,不高兴了便杀你吃肉。”
“而今王室衰微,诸侯战乱不休,若想在这大争之世立足,岂能将性命交付于他人之手?”
时秋看向她。
这个师妹面貌虽然柔美,也常常爱哭,性情却刚毅坚贞,认定的事从不回头。
再看自己,虽争强好胜,却总是徘徊不定,难下抉择。
“过去,你辨难也总是胜我。”
时秋仰起头,将壶中的酒饮尽,方才定心。
“嶂城被破前,族中曾找过我。”
并不是有意将傻子放在城中晾了两日,而是为族人所拘,脱不开身。
“他们告诉我,旧襄乱党步步紧逼,余下几家世族预备殊死一战。”
禾女闻言一惊,却又问:“师姐隐居多年,他们怎么想到要来找你?”
“正是我隐居多年,他们大约觉得我在嶂山结交甚广,欲寻奇人助阵。”
“师姐怎么说?”
“我说,嶂山云遮雾绕,任你住上十年八年,照样半旁个人也见不着。帮不到,让他们另请高明吧。”
“他们可信了?”
“他们?”
时秋哂笑了声,“他们自然不信……不过,这奇人也不过是个添头,我看他们似乎还有别的打算,只是守口如瓶,见我不帮他们,便半个字也不曾透露。”
禾女皱起眉:“自世子攻伐以来,已连下二十七城,白华孟陶四族又占六城,除却旧都川瞿,余下十二城虽与靖国相近,可靖却并未大兴出兵抵御。”
“这些所谓的世族,昔年国战连粮草都不愿出,如今倒是敢出城迎战了,也不知是谁给的胆子!”
她越说越怒,却陡然顿住。
片息后,她忽然自问一句:“是谁给的胆子?”
西戎
“是西戎。”
戚言坐在案前,捧着手炉。
身边的火炭也正燃着,发出“哔剥”
轻响。
神医与她对坐,正抚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