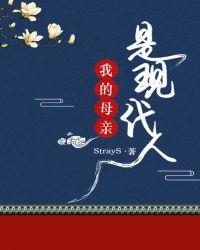爱上中文>我成了新帝的外室免费阅读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姜怀央看得哭笑不得,一边要她慢些用,一边向她那边递了递斟好的花茶。
小娘子是个好动的,连用点心时也不安分。她仗着他屏退了众宫人,眼下屋内只有他们两个,便玩起了椅子的扶手。
玩着玩着,忽地发现自己将双腿卡进扶手间,出不来了。她困窘得耳尖通红,也不好意思向他求助,只好兀自尝试着脱困。
最终出是没出来,自个儿反是急得眸中氤氲起水雾。
其实姜怀央早注意到她的窘况,不吱声,便想瞧瞧她什么时候才会向他开口。
“夫君,帮我——”
小娘子终于愿意向他求助,语气可怜极了。
她总是勾人而不自知,姜怀央暗自叹口气,起身来到了她的跟前,“还乱不乱动了?若是我不在,你便叫宫女来救你吧。”
她可劲摇头,“下次不会了。”
她口中服软,心下想的却是,如果不是知道他在自己身侧,她又哪里会这般不规矩。
他原是打算环着她的腰肢,将人抱出来,可手一碰上那腰上的软肉,又变了主意。眼下小娘子也动弹不得,却是无需那红绳了。
他以为自己从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于是他放在她腰上的手又松了开。阮玉仪心下一凉,以为他是不打算管自己了,于是一把扯住他的衣袖,好叫他不可离开自己半步。
因着小娘子受了寒,眼下虽未入冬,宫中便早早用起了炭火,所以她便是只着一身轻薄襦裙,也不会觉着冷。
这会儿她双腿被卡在扶手中,且为大开状,裙摆被捋得上来了些,露出她纤细的脚踝,以及上边一串金铃足链。她还在徒劳地微微动着,试图从里边出来,晃得铃音细碎响起。
姜怀央眸色幽深,摁住她的肩,不让她乱动,“要我帮你,总归得给些好处吧,娘娘?”
阮玉仪一听,便知道什么好处最是有效。她捉住他的衣襟,使他俯下身来,快速地在他唇上印了下,便急着命令道,“快帮我出来,若是待会儿有人进来见着了,我的威严就没啦。”
闻言,他忍不住低笑一声,就她那骂人都翻来覆去只有几句的,皇宫上下,哪有几个怕她的。
“就这点贿赂,娘娘未免小气了些。”
他轻笑,将那一吻加深。
她被固定在椅子上,心下无助,生怕自己摔了去,只得搂紧他的脖颈。
……
姜怀央退了朝,他还是觉着自己脑中有些昏昏胀胀的,也无心细细辨别那些大臣的嘴一张一合说些什么,连两派人意见不和,争论了起来,他也由着他们吵去了。
下边群臣见新帝默然不语,沉着脸,反倒是无需他说,也逐渐安静了下来。
忽地意识道殿中已是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落在他身上,姜怀央简直怀疑他们是否知晓了自己在想什么,心下一跳,面上却是如常,悠然道:
“争完了?明日之前汇作一份奏折呈上来——听得朕头疼。”
群臣却全然没有发觉他们陛下的异样,生怕他发怒,为首者忙应了下来。
程府东厢房。
阮玉仪落下香囊的最后一针,松下一口气。
将东西举在眼前打量,上边用嫩黄的丝线绣了金桂,这些小花被安排得错落有致,形态圆润可爱,一瞧便是小娘子用的东西。
她心中忽地没底起来,如此小女儿家的物件,也不知世子是否会喜欢。可她除去为兄长绣过荷包之类,也着实没为旁的男子做过这些。
兄长自然是只要是她送的物件,都好生爱惜着。因此她虽见过男子用的纹饰,却不曾绣过,思来想去,还是挑了自己擅长的。
一边的木香笑道,“小姐的绣工真是极好的,真是便宜了世子爷。”
被戳中了心思,她面色一红,嗔道,“你这张嘴真是惯会胡说的。还不去将那晒好了的桂花取来?”
木香笑着应下。
不一会儿,一瓷罐的桂花干便呈了上来,她轻轻揭开盖子,里边馥郁的香气便扑面而来。桂花虽小,可这香气,比之那些大朵的花却丝毫不逊色了去,阮玉仪心中满意。
她捏出罐中的小匙,一手将香囊口子撑开,一点一点将东西舀进去,将里边填充得鼓鼓囊囊。她又舀了一小勺那木槿香囊中的药粉出来,混了进去。
如此,药末的苦味冲淡了金桂的香气,嗅起来像是上好的花茶,自最初的馥郁过渡到苦涩,余韵无穷。
她知晓世子夜里睡不安稳,只希望着胡人的药粉混入里边,叫世子偶尔嗅着,起上些安神之用。她知道这小物件不值多少银钱,但总算是不白吃他的荔枝。
桌底
阮玉仪将抄好的经文与香囊一并带上,动身去找世子。
院子里边并没有人,她思忖了片刻,将经文搁在佛堂中,香囊则贴身带着。小坐了片刻,便见一玄衣公子推门而入,他身量修长,气韵清冷矜贵。
今儿是个阴天,可咋一眼瞧去,倒像是他周身的清冷逼退了光线,使之不敢近身。
阮玉仪不慌不忙地起身,盈盈一礼,“世子殿下。”
只见那人微微颔首,算是应过了,却不向她这边来,而是往一边的厢房去了。随在一侧的温雉冲她笑了笑,道,“姑娘也进厢房罢,这天怕是要大雨。”
听了这话,她不由仰头瞧了一眼,果真见头上一片乌压压的云,再往远处瞧,那边的天却还算是澄澈。
确实像是要下雨的模样。她不再说什么,也跟着进了厢房。
姜怀央正垂首看着书,当她迈过门槛的时候,他刚巧翻过一页。她犹豫了会儿,将木凳移偏,于他近处落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