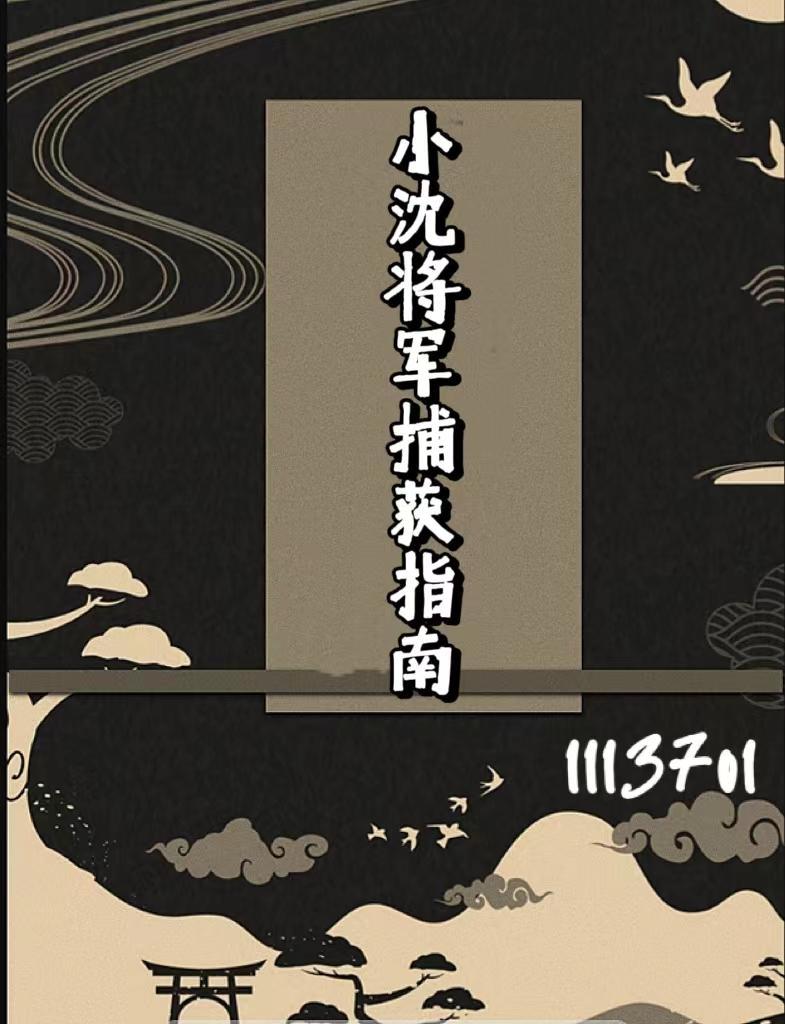爱上中文>天行九歌和秦时明月什么关系 > 权力之属(第2页)
权力之属(第2页)
“姬无夜的人尽是些贪财又无法无天的蠢货,绝对不会放过偷盗库中财物中饱私囊的机会,而红莲殿下绝不会允许可爱的小姐被一群粗俗的恶人欺负的。”
“所以……我们坐上观虎斗就是。”
坐在正堂的主位上,森罗的手掌轻轻按在还没完全愈合是伤口处,“看样子又要留疤了。”
“小姐不必在意,祛除疤痕的药方并非难求,属下定当尽力。”
蓑衣客柔软的嗓音中带着轻松地玩笑。
“呃……你脑子里都装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森罗抬头,表情中透着一言难尽的惊讶和古怪,“一道疤而已,留着就是了,干嘛要浪费人力财力去做这种毫无意义的蠢事?”
“可……可小姐终究要嫁人的,留了伤疤难免会……”
哈哈哈……啊……嘶……疼疼疼……
忍不住的大笑牵扯了伤处,出一阵剧烈的疼,刚刚笑容满面的森罗立刻白着脸疼得蜷缩在椅子上,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乐极生悲。
“小姐!”
“别急,我没事。”
森罗制止了蓑衣客的动作,等疼痛缓过劲儿来,缓缓起身触摸着墙面,描摹着那崭新的刻痕,那曾经以为被所有人都认为不可企及的奢望,却就这般在她手中被缔造为现实。
“这是一个剑与死亡的时代,是男人的时代,所以男人可以通过武勋彰显力量并获得于此相衬的权力。
可无法稳定延续的权力意味着动乱,所以男人们迎娶妻室以求血脉的延续,又用严苛的礼仪宗法保证权力的顺利过渡。
因此,女人想要占有权力就必须先成为一个妻子去影响她的丈夫,或是成为一个母亲去控制她的儿子……”
森罗走到蓑衣客面前,却突然娇笑嗔斥道,“而你们男人~一般将这样的女人称为——祸水毒妇!!”
“小姐,属下绝无此意!我……”
蓑衣客正要解释,却被森罗伸出的食指抵在了唇前。
“我知道,就算你有也无所谓,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没必要再去走这条老路了。”
举步登楼,森罗倚栏四顾着新郑的四周的城楼,“这是属于我的权柄,我会让蒙尘的宝剑再次焕光彩,在坍塌的废墟之上重新建起壮阔的城邦……”
森罗展开双臂,绣着飞鹰的青色衣摆在风中鼓动,仿佛曾经在战场上飞扬跋扈的战旗。
在蓑衣客眼中天地之间仿佛只余这一抹明丽色彩,一股骄傲悠然而生。
是啊,就算是女人又当如何?玄灵军的主人自当傲立于天地之间为天下敬畏,岂能成为折翼的鹰落入金笼之中!
“殿下……”
不知何时去而复返的藏青脸色极为阴沉难看,“血衣侯白亦非明日要登门拜访……这是拜帖。”
“他居然还敢来!!”
刚刚喜不自胜的蓑衣客立时变得暴怒如雷,将那张印着血衣侯家徽的纸撕得粉碎。
“回帖,让他明日登门吧。”
“小姐!!”
“来者是客,我刚开府就将一位侯爵拒之门外,未免让人觉得没有教养,会坏了镇南侯府的名声。”
“而且……”
森罗捏着手中的黄铜令牌,那只栖身在深雪中的幽蝠……真的背叛了振翅长空的雄鹰吗?
当初生的一切,似乎还有很多疑点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