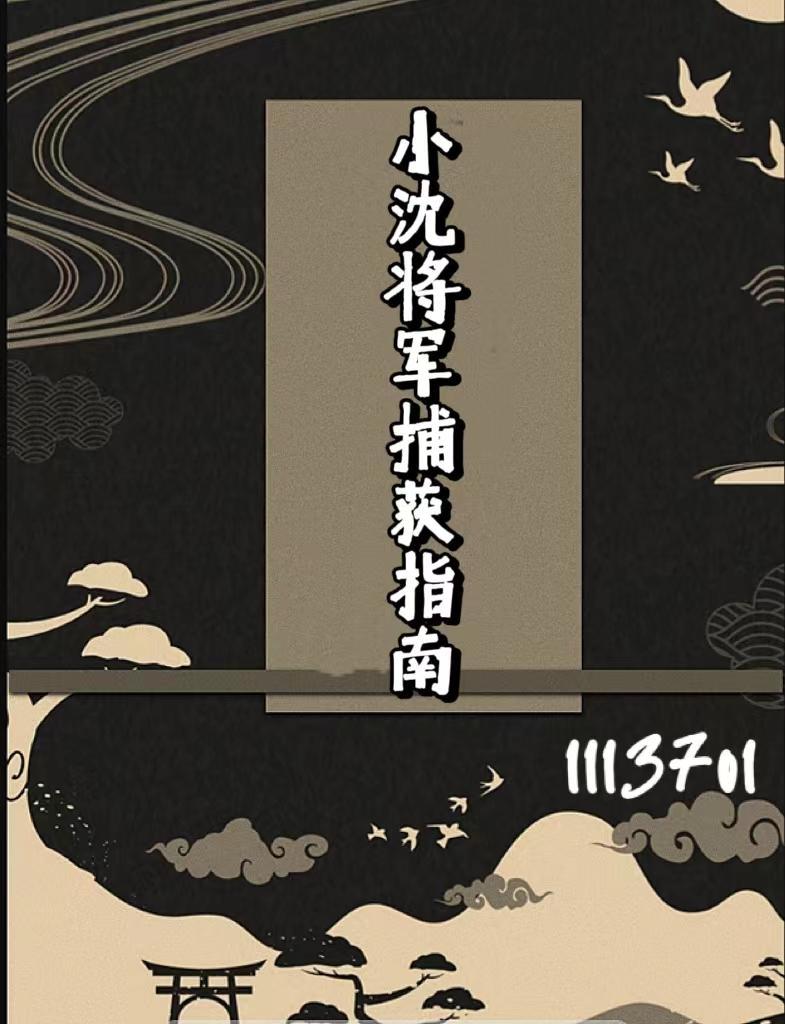爱上中文>风雪夜归人翡翠多少钱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片刻之后,兑一的毒大概是起作用了,巨鸟的身子开始在空中摇摆,越飞越低,直到与树平齐,少白想要先化作鸟身悄悄溜走,谁知道即便如此这只疯魔的臭鸟还是不撒爪。
白毛怪孤身径直朝那巨鸟撵去,脚下踏着树冠,蛾眉冒着耀眼荧光如似他心中不可熄灭的怒火,一刀下去断其双足,少白得以化作飞鸟离去,巨鸟朝天嘶吟,愣是扑扇着翅膀又挣扎着高飞了一阵儿,大抵是疼得不行,紧接着整只鸟带着刚刚翻身骑上鸟背的白毛怪一头扎进了距离老远的半山腰林子里。
他尚还坐骑在鸟身之上,降落之时被树枝划破了脸颊和臂膀外侧的许多皮肉,眼瞧着一块肉赘在肩头,痛感拉扯着他身上每一条神经,只要轻轻一动,便好似有人按着身上的伤口拉拽,即使如此,他强迫灵力聚在蛾眉之上,落下了第二刀,一股黑色的腥臭血液喷溅在他脸和衣袍上。
倒也不妨事,意料之中,那些伤口正聚拢来四处的白色荧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他还挂念着少白,散去蛾眉便要往山下走。
虽有些疼,但尚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万万没想到的是起身刚迈出两步,如潮水般望之不尽的汹涌痛感突然一并朝他袭来。
一眨眼的工夫,疼痛被拉至极致,顷刻席卷全身,顺着他的经络传遍身上每一处,从五脏六腑蔓延至肌肤的每一寸,埋藏在皮肉之下,是按揉也按揉不到的位置。
猝然跪倒在地,而后重重摔下,双臂环抱蜷缩着的身子,大抵是太疼了,从心里向外透出刺骨寒意,好似被丢进了冰洞里。
原本该一片空白的脑子里闪过一些连白毛怪也不知该是熟悉还是陌生的画面,一条黑龙盘踞在雪山之上,卧在雪地之中,鼻息里冒出腾腾热气,鳞甲映着天空太阳的绚烂色彩,遥遥望去似是五彩斑斓。
一幕幕似是残影,却又好像即使画面不完整还是能靠着一些莫名的意识将其补充,睁眼之时已是双目血红瞧不见自己身处何地,随便朝着个下坡的方向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在一棵棵树之间来回狼狈折腾。
已然磨蹭到了崖边,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跌下去,他仍是什么都看不见,青天白日里出了鬼,周身生着带刺荆棘,双眸之下却是寒风刺骨的雪原,最后落在绊脚的青石上,就同被抛出的蛾眉,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由此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不知就这样下降了多久,被身体上的疼痛和毫无缘由的感伤折磨得不成样子,无数情绪在内心拉扯,糅杂成一团,全部塞回他的身体里,任由其降落,就算最后碎尸万段,血肉大概还是会一片片、一块块长回来。
现实却不若他预想的那样糟糕,耳边簌簌疾风忽然停了下来,兴许是树,他没敢想拦住他下降的竟是少白。
振翅如利箭第一个冲到山上去,在白毛怪落崖前最后一刻,看见了个浑身脏污的灰白身影从山崖边上消失,便也一同俯身冲了下去,触到他的一瞬化作人身,巽二在崖壁上留下一条长长刀痕,终于在两块石头的夹缝中停了下来,少白一只手握着巽二,一只手揽着白毛怪的衣裳,两人在悬崖边挂着,看起来只要一阵风就能将其吹落。
“朔月……”
“朔月……你看看我……”
“朔月……”
白毛怪觉得脑子里有一个模糊声音一直在不停反复喊着些什么,而他只能在一片黑暗之中焦急万分,什么都做不了。
“隐!”
“隐!你看看我!”
“隐!”
少白的脸憋得通红,胳膊上的肌肉绷得很紧,既不能倒出手来将其抛到崖上,又不能放开手以求自救,更何况他如今好似个活死人一样,瞪着一双通红的眼,无论喊什么都没有回应,还不如大狱里三四百斤的铁链省心。
崖壁的石头看起来已不再牢靠,一阵阵往崖下滚落着砂石碎屑,巽二通体闪着荧光,它从未如此强烈过,连靴筒里的兑一也有了感应。
虽说白毛怪能自愈,但这悬崖这么高,就算不摔死也会疼死,她断然不能眼睁睁瞧着他碎尸万段还无动于衷,更何况白毛怪是为了救自己才落入如此险境。
眼见着匕首所插之石裂纹越来越长,少白有些绝望,“死就死了吧!”
带着些许不甘怒吼了一声,用尽全身的力气抱紧了他,两个人一上一下相拥着坠入崖底,巽二紧跟其后,追随少白而去。
耳边的风又吹了起来,这才唤醒他,何为现实,何为虚妄,冰凉的怀里拥着个滚热娇柔的身躯,鼻息之中是熟悉的味道,少白已然合上了双眸,而白毛怪却是睁开眼也什么都看不到,仅凭着直觉在崖壁上蹬了几脚,落地之时少白的耳边传来一声闷响,周遭扬起一阵沙尘,好似仙人腾雾。
缓缓睁开眼,不若她想象的断胳膊少腿,只是最初在崖壁上擦伤了几处,甚至身子下还软和得很。
烟雾弥散之中一阵阵虚虚实实白光若隐若现,似蜿蜒的蛇顺着白毛怪身体里的经络向心脏处爬行,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没了意识,尽管如此还保留着一分执着,少白想要起身,手掌撑着地面,一连试了三次却都没有成功。
白毛怪的手仍环在她背后,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只好化作鸟,将身体缩小许多才得了空隙,向山崖之上望去,自己见到白毛怪时云起与云霓都还没有赶到,现下大概更是想不到落崖了吧?
她大腿上还有那只巨鸟留下的伤,虽然不重,但背着毫无意识的白毛怪,还是走一步疼一下,伤口裂开,本已经凝结的血,又一股股淌出来,走不了多远,好在崖下有个石洞可供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