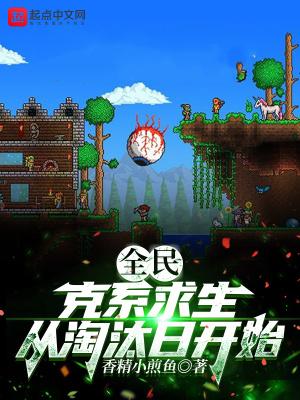爱上中文>贺月舒贺云霆最新章节更新时间 > 第103章 贺云霆觉得沈黎川是懦夫(第2页)
第103章 贺云霆觉得沈黎川是懦夫(第2页)
沈黎川不计较这点礼数,事实上,从太早以前,贺云霆对他态度就谈不上好。
他几步跨到桌前,“为什么不放过月舒?”
贺云霆手肘撑在桌面,拊掌,“好问题,你又是从哪得知我没放过她?”
沈黎川不踩他陷阱,“她这几天不出现,是离开了对吗?你在贺氏针对贺伯父那一番动作,是伯父发现,并阻拦了,是不是?”
贺云霆眼睛如同一张网,用他的城府,阅历,老辣编织的结实莫测,直勾勾罩过去,没有几个人能躲避。
沈黎川毛骨悚然,强撑着,忽然想到月舒。
想到,她这四年是不是也经受着这般锥心剥骨的逼视。
如果有,她要怎么样才能坚持抗争四年。
没有被击碎,没有被污染,从不堕落。
她所思所想依旧妙趣横生,世界在她眼中千奇百怪,每个人进入她内心世界,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
他视线中忽然出现月舒,黑檀木桌子倒扣的相框里,月舒站在没过脚踝的溪流里,岸边水草青青,蔓长的枝条在水中轻抚她的脚趾,阳光射出粼粼的波浪,她比波浪还晶莹。
她在笑,明媚又灵动,稠白的肌肤,也是流动的,是一汪比溪水澄静的春日湖。
谁见过她,谁能忘了她。
贺云霆猝不及防收回相框,照片那面对着自己,粗糙的背面对他,
沈黎川,“什么意思?”
“我的女人,你盯着看,我还没问你什么意思。”
沈黎川表情凝固成石,荒诞,虚妄,无稽,惊悚,最后反应过来是可笑,“你的女人?你喜欢她?还是占有欲?”
“你觉得呢?”
沈黎川根本不想深究一个无耻之徒的内心,他只抓紧机会,“如果你喜欢她,更应该放她走。”
贺云霆面容浮显一层嘲讽,像对待迂腐的书生,愚昧念经的僧人,空谈误国的囊臣。
他对沈黎川,总是喜欢这种——沈黎川努力辩解,疏讲道理,最后被他驳倒的场面。
“喜欢她,就应该尊重她的意愿,是放手,是希望她活得顺心快乐——”
贺云霆这次却连完整的话,都不愿听,摆手打断,“你觉得自己喜欢的很理性,很克制,甚至能放弃她,很伟大?”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是我发自内心对她的小心翼翼和不忍打扰,我对她一日不曾减少,但我会克制,喜欢一个人,要为她着想。”
“你这是懦弱。”
贺云霆面目不起波澜,眼底郑重,坚定,一往无前,空前自盛,爆发出来的光,像一把灭世的火,悍然,霸道,暴烈,烧起来穷尽一切。
“你爱她,刚才却连一个爱字都不敢提,你想做她的白马王子拯救她,却瞻前顾后,是蒙着眼睛的驴,四年都不敢抗争。”
“你说放手?”
贺云霆眉眼带笑,好笑的,鄙薄的,在这满屋沉黯中,犹如亮锋出鞘,锐不可挡。
“你当然要放手,你冲不破家世困扰,无能。放不下骨肉道德,愚夫。更别说什么尊重她,你不过是怕面对违背她意愿后,她愤怒的目光,你承受不了她厌恶你,怨恨你,却舍得把她后半生交到一个素未谋面,未知的,不如你的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