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文>人类怎么看到光年以外 > 第37章(第1页)
第37章(第1页)
言克礼温柔地问:“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让你泄愤,如果不能的话,还可以让你再来一枪。”
指缝上的血还在往下滴,言克礼却感觉不到疼痛一般,当真要把枪交到女人手上,“不过只能打左手哦,右手还要照顾人,所以不太方便。”
女人的反应与众人如出一辙,只是纱布限制了她的面部活动,她就这样愣在原地,看着言克礼的枪好半天没说出话。
“来吧,这还远不及你的痛苦。”
言克礼又往前递了递,“别错过这次机会。”
“算了,算了,”
女人推开他的手,径直朝前走着,嘴里不停呢喃:“算了,算了……,”
就这么消失在了病房门前。
“中将!你怎么这么冲动!”
张景回过神来,如履薄冰般捧起言克礼的左手,“医生呢!赶紧过来包扎一下!”
“好了,没事,我有分寸。”
言克礼收回枪,低头敛眉看了眼手里的窟窿,神情与方才柔和的模样判若两人。
他让医生简单消毒上药后就离开了,张景看着他的背影,头一次生出他很脆弱的想法。
他一定是看错了,中将可是当年新兵军事综合考核的榜首,不仅开得了战机,还能驾得了航母,百米之内,猎杀活物绝不需要瞄准第二枪的神枪手。
联盟史上最年轻的中将,如果不是现在这种环境,原本可以风光无限的他,凭什么,凭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来诘责他,凭什么他什么都要解释,凭什么他要承受这一枪!
在这个位子上,他得到了什么?
钱财吗?权力吗?荣誉吗?
未必,只是张景想不出来。
相比于张景的不忿,言克礼倒是觉得那一枪让他舒缓了许多,至少他不用再费口舌去跟那人解释。再说了,他能解释什么,解释他是真的无法一心二用,因为他想救的人他自己都没找到,解释他在车上打了几个电话,解释他在车上不能开枪,因为一旦开了洞口,那群恶臭的老鼠就会立即涌进车里把他撕掉,解释确实是他失职,因为他没那么神通广大料到老鼠会产生报复意识且和人一样做好了计划,解释他不应该让老鼠在城区底下挖了那么大一个坑,而他等到人家把坑都挖好了还没发现。
太累了,连轴转的工作早就逼的他精神压力达到了一个阈值,他已经疲于应对这些接二连三的问题。一个子弹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要用嘴?一次如此严重的失职,一个子弹的惩罚已经很轻了。
压抑了这么久,差点就以为自己真是什么青天大老爷了呢。
再者,他还要回去看洛晏清,哪有那么多时间可浪费。
想念
洛晏清睁开眼时,屋里并没有人。不久前才造访过的房子并不陌生,他对于自己出现在言克礼房子这件事,也没有了太多的惊讶,而且他居然还有种「我果然是在这」的感觉。
躺在床上回想了自己晕倒的事情,洛晏清才想起那个堪称混乱的夜晚,又后知后觉自己好像被老鼠咬了一口。脑袋在松软的枕头上左右转了转,果然看到了被包扎着的左臂。本来没看之前还不觉得什么,现在看之后,那里的痛感就也跟着视觉一并传进了大脑。
简直痛得他想骂街,可现在他渴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渴到怀疑自己睡着的那几天根本没人给他喂进去一滴水,要不然他怎么觉得自己的嗓子能冒烟?
不过话说回来,他这次又是睡了几天呢?
正思考着,外面就传来一道短暂的滴卡声,条件反射下,他双手撑着就想坐起来,可他忘了,现在自己左臂上少了一块肉,根本没办法支起他的身板,反而又扯到了伤口,疼得他倒吸了口气,眼里甚至泛起了泪花,接着又重重地摔了回去。
言克礼刚进屋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祖宗,你可算醒了。”
言克礼开着玩笑走过来,有些别扭地用右手摸了摸他额头——早知道打右手算了,他突然后悔。
“感觉怎么样?”
言克礼刚问完,眼睛随意一瞟,就瞟到了纱布上渗出的丁点血迹,脸又迅速黑了下去,“不好好躺着,乱动什么?”
“我想喝水,”
洛晏清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好渴。”
言克礼测了测对方脸上和脖子的温度才撤回了手,觑他一眼,无奈中又似乎夹带着宠溺:“你真是我祖宗。”
温水很快送了过来,洛晏清这会靠在床头,伸手去接杯子时,注意到言克礼的左手也绑着绷带,“你也受伤了?”
他以为对方是在那天晚上受的伤。
“是啊,咱俩都是伤患你还心安理得的指使我呢。”
言克礼在床沿边坐下,问他:“怎么伤到的?”
洛晏清为他前面那句话小小羞愧了下,接着就跟他讲了当时事情的经过:那天他刚从电梯出来就发觉到了楼体在微微摇颤,这个时间点甚至比言克礼察觉到时还要早上那么几秒。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感官,于是第一时间去敲了祝平安的门,祝平安当时还在厨房给自己煮早餐,没能及时听到声音去开门,耽误了点时间。
后面他出来时,洛晏清又尽可能地提醒了附近几间房的人,让他们赶紧逃命。紧接着广播站就响起了通知,原本宽敞的楼道瞬间被人群占据,大家都疯狂奔向出口,唯恐慢了一步就会被压死在楼里。但这么多的人同时挤在一起,你推我我推你,没有人指挥秩序,很快就有人倒在了楼梯上,而大家顾着逃命,根本不会在意脚下踩到了谁。洛晏清他们在往下跑的时候,注意到了地上有两个摔倒的女生,几乎没有过多犹豫,两人就默契地一人背起了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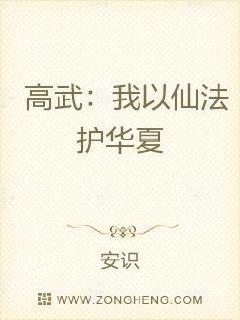
![[综漫]外挂是美食小游戏](/img/18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