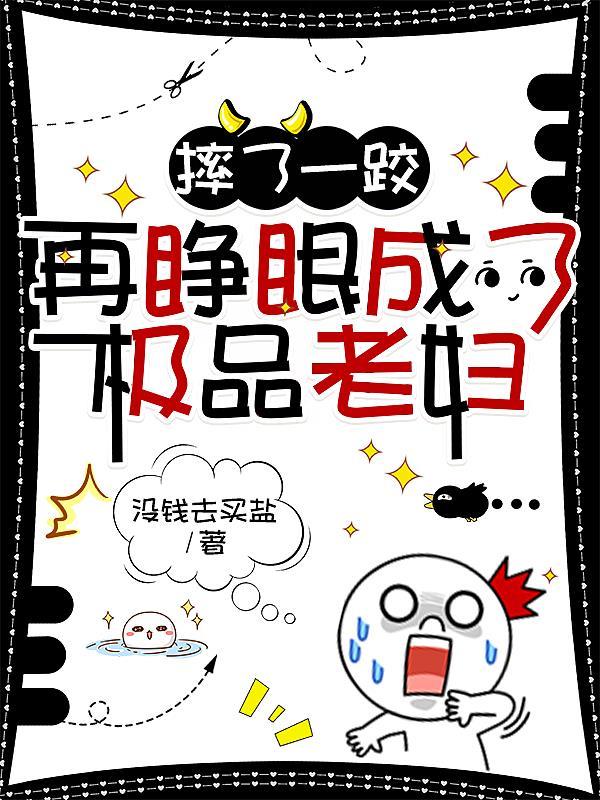爱上中文>愿此生长情 > 第56章(第1页)
第56章(第1页)
“隔壁街的刘婶,来给你说媒的。”
柳永安放好东西,整理好衣着端坐在另一边道。
“哦什么!!!”
“哎呀,柳老爷,别来无恙啊!”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年近五十的刘婶一边说着,一边夸张的扭着腰肢从门口进来。
柳晟刚要起身,刘婶突然双眼放光的窜到柳晟身边,嘴里发出哟哟哟的惊叹:“哎呦喂,柳老爷,想必这就是小少爷吧,啧啧啧,长得真是一表人才,怕是将咱们这最漂亮姑娘都比下去了。”
被转着圈打量的柳晟双手交迭放在小腹上方僵硬的站在原地,刘婶的大红手帕在他眼前不停的晃来晃去,晃的他直想吐,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就只能站在那里眼神坚定的目视前方。
“看看小少爷这双眼睛,啧啧啧,这眼神一看就是能成大事的,就是不知道哪家姑娘能有这个福气。”
刘婶越看越看越满意,看的移不开眼。
刘婶话密的柳永安几次想开口都没能说上话,现下趁着刘婶在思考哪家有好姑娘的时候,柳永安终于将卡在嘴边的话说了出来,“多谢夸奖了,只是我这儿子从小就体弱,三步一小喘,五步一大喘,七步就要倒,吹不得风又晒不得太阳,吃了上顿就吃不下下顿,躺下了半天起不来身”
柳晟站在旁边听的一愣一愣的,有那么严重吗?虽然三分有十分的夸大,但柳晟心领神会,立马配合他爹的这番话,开始咳了起来,且在刘婶疑惑的探究中咳得越发卖力,最后咳的喘不上气两眼发黑一屁股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这可把刘婶吓一跳,连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忘记了,赶忙就要走,走之前还好好言语关心了柳晟一番,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养病,养好了她再来,说完甩着她的红帕子急忙忙的出了门,生怕柳晟一个不小气就过去了。
“行了,别装了,人走了。”
柳永安幽幽出声。
柳晟一个深呼吸,待缓过来后重新坐好,看向柳永安心里百感交集,良久,发自内心地说道:“多谢父亲。”
柳永安也是语重心长:“谢什么,就没指望你延续香火,这样总比刀架在脖子上了才被人发现你不行要好,我可丢不起那人,臭小子。”
大军行进半月,终于是在年前赶回了京城,回宫复命前,谢鹭安先行让他们回家和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过个好年,自己则是独自回宫面见。
谢鹭安回到太子府的第二天,宫里连降几道圣旨褒奖太子,流水一般的奖赏进了太子府,谢鹭安正式接管兵符成为实至名归的大将军。
伴随太子大捷的余热,新年里,京城里比往年还要热闹,连最偏的小巷子里都挂起了三两明晃晃的灯笼,照亮了一直被遗忘的角落。
整个新年间,太子府也是门庭若市,恭贺的人踏破了门坎,谢鹭安一边为着宫里的部署焦头烂额一边还要抽出精神应对上门的官员,成为了整个京城最忙的人。
北方的一处寨子里,门外大雪纷飞,谢恒与谢宸面朝门外并排坐着,炉火上的茶壶里热茶滚滚,满屋飘香,俨然一副闲情惬意的画面,可画中人的脸上却是愁云惨淡,不见悦色。
谢宸从年前被接过来到现在一直心事重重,烦闷郁结,人也总是蔫蔫的,谢恒看着谢宸消瘦的脸,“二哥就在这住下吧,别回北疆了。”
“要回的。”
谢宸抬起沉重的眼皮看向门外,气息微弱,但话却很坚定。
谢恒看出了谢宸眼底的决心,没再多说,只是端起热茶喝了一口,腹诽道:嗯嗯嗯,但愿你说的是回北疆。
连绵不绝地大雪下了一个月才稍有停歇的迹象,这一个月里谢宸依旧是心不在焉,一天里有半天都是看着屋外出神。
不忍心看着谢宸这么颓废下去,谢恒和郑安南想法设法的想要安慰他,但谢宸始终说不出来自己是为什么这样低迷,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该说清楚的都说清楚了,但还是不能释怀。
三月初,北边的雪一停,谢宸就离开了寨子,谢恒站在寨口眺望着谢宸消失的方向,对着旁边的郑安南唏嘘道:“也不知道这么着急是要赶去哪里”
“听你这话,宸儿不是要去北疆?”
郑安南疑惑的扭过头。
谢恒耸了耸肩,双手一摊,“谁知道呢?”
与此同时的京城谣言鼎沸,闹得人心惶惶。宫里传出陛下早朝时突然昏厥,经太医诊断出说是积劳成疾,病已入肺腑,怕是时日无多。
从谢兆晕倒到谣言满天飞不过半个时辰,一应官员都在殿前,无人出入宫门,那么事发的消息是怎么传到宫外的?甚至太医还没见到谢兆城外就已经在传当今陛下命不久矣了。
于其说是传出去,倒不如说是预测。宫外有人提前预知到今天早朝会发生的事,他只需时间一到,将消息不小在宫门外说漏嘴即可,剩下的就交给它自己发酵。
重华宫内,几位肱骨老臣围在床边,等待着太医院院判的诊断结果。
谢兆双目紧闭,毫无生气的躺在床上,看着一副垂死之相。张院判紧拧着眉叹了口气,摇头道:“哎,怎会如此。”
众人闻言脸上皆是一阵死寂,整个寝殿内落针可闻。站在最后的周谏拨开人群,挤到张院判面前,将张院判一把拎起,满脸悲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怎会如此,如此是怎样,说清楚!”
周谏像是气急败坏一样,拉着张院判的衣领子不肯松手,而且越来越用力,见形势不对,站在一边的谢鹭安上前将两人拉开,安抚道:“周大人稍安勿躁。”
说完扭头去问沉默良久的张院判,“张院判,父皇他到底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