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文>将军妻不可欺下拉 > 第62章(第1页)
第62章(第1页)
再说那穆枭,假意与假无璧辞去,转身快走至后院与苏雅交代日常。
苏雅已知身份暴露,还又被穆枭发现,本是又气又羞,回府之后又见穆枭没有来追,反而有心同那北境公主说笑,心中更是憋屈。
这时跑进后院,左手随意抽起一根竹条,于空左右挥着打着挡路的叶子置气。
穆枭从后赶来,知道苏雅有气,并没有避让,谁知苏雅一个转身就将竹条抽在了他的身上,好大一声响。穆枭当即就撕拉了一声,露出苦色。
苏雅心中瞬时起了愧歉之意,可关心也不是,辩解也不是,总未开口,只怔怔看着他,那竹条从他耳边抽到肩上,现已生了一道红狠挂在耳上,似有出血之相。
穆枭倒没生气,只是握住了竹条的另一端,本也是轻轻悠悠抽出来,却不想无意之间也划伤苏雅的指头,引得她也叫衰一声。
穆枭忽的着急,凑上前去,嘴里都是抱歉:“我不是有意的,让我看看,是不是竹刺扎进去了?”
说罢便捧握着苏雅的左手,细心为她挤着刺。
苏雅与穆枭亲近一会,脸就羞得飞红,忙得抽出手,又往后退一步,反嘴抱怨:“这下又扯平了!你果真爱报复人!”
穆枭沉了口气,拉牵着苏雅的手腕,朝她屋里走。苏雅起初还做做样子反抗一番,却因穆枭握得紧渐也不挣扎了,由着他带到他的房里。
穆枭进屋就拿出药箱,欲意为苏雅针灸右手。
“会有点疼,得忍忍。”
穆枭虽没解释,苏雅倒也信他,见他时针的阵仗与那些长着白胡的老医者颇为相似。
忍不笑出了声。
穆枭见状,反而纳闷:“这也不是笑穴,难不成师姐穴位与常人不同?”
苏雅听穆枭如此称呼她,忽的又偏了头,敛收了情绪。
穆枭见她失了说闲话的心思,便钻心施针,只在一个穴位上,来回缓缓深刺,直至苏雅的右手不自觉一张一缩。
穆枭解释:“此穴刺激手掌经络,若每日如此,或可加速右手复健。”
,边说边在苏雅右手穴位之处点了一颗红砂痣,且又在针上做了记号,方便她知晓入针几寸。
苏雅见他费心至此,正有古怪想问,却听他自答:“后日我会和北境公主出行,半月后方归,你趁此疗养,倒不是盼你恢复几成能帮忙击破她阴谋,只是盼着你可自保,不叫我和萧侯费心。”
苏雅自揉右手,心里原不舒坦穆枭同假无璧出去,偏是装作置气旁的事,幽幽说道:“我现已不大中用了,定会躲得远远的,不好成了那破烂拖油瓶,碍你们的事。”
穆枭无奈笑道:“你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知你不是在气这事。可是眼下需要拖延时间,让萧侯把北境蛮夷番王请来盛京好把这公主带走。我心里虽也是恨她,若我们私自处决捆了过去,倒显得大朝蓄意挑拨关系,有理反而成没理的了。眼下只能哄着演戏了。”
“你哪是演戏,分明真情流露!”
“那你可是吃醋?”
苏雅见她心思已然被穆枭看穿,只侧身坐着,不与他对视,垂眸玩着十只手指,心不在焉,一时不想走,却也不知道留下说些什么,该与他交代什么。
穆枭突然轻声问了一句,“若我没发现,你会想着有朝一日同我坦白吗?”
苏雅听此,心中明显被揪紧了,想起自己本来的顾虑,又念及受圣上掣肘,原也没想好说或不说,现今被问此自然也答不上来,只得沉默。
穆枭见苏雅闭口不谈,两眼略过失望,自笑道:“师姐愿意告诉萧侯,却不愿意告诉我,想必是觉得我不好信任。也是,初见之时我便对你如此无礼又恶言相向的,你心里自然多恨我三分,不容易信我是自己人。”
“我原也不气你,都是我自己种下的恶果罢了。”
穆枭边说边收拾医箱,自己走了出去。
苏雅本就心烦,更是得了圣意知假无璧的身份特殊,更不好动她,亦不想见到穆枭同假无璧两两不知谁情真谁情假的做戏。
眼不看心不烦,索性去了萧侯府躲两天心事,把穆府彻彻底底留给他们。
萧衡见苏雅带了行囊来,赶忙欢迎,说道:“正想去请你,你自个儿来了倒好。”
苏雅分外客气见礼,倒让萧衡不好意思,又反复明说:“真不是我告诉他的。”
隧恭恭敬敬将苏雅请了过去,引去见张缤。
张缤见苏雅来到十分惊喜,上前挽着她手关切道:“我见你那日受好重的伤,头几天本不敢去打扰,后听闻你好了,侯爷也不让我去,说是穆府来了坏人,让我躲远点。”
苏雅略点点头,对张缤亦有亏欠:“终究是因我聪明自负,引得嫂嫂那日受苦。”
“混说什么呢!”
张缤笑着嗔道:“都是命里注定的事。我算是看开了。”
而后又摆摆手,吩咐颖儿道:“今儿苏小妹来住,快去把我厢房里的被褥枕头通通换新了,晚上我就同她睡一屋。”
“诶,我还没走呢!”
张缤白了萧衡一眼,没有理他,领着苏雅边走边说:“你不如快些走,倒还能快些回。净在磨蹭,还混说事情重要,不得外泄。”
生疑(九)80
且说苏雅至侯府修养,与张缤作陪,二人在同睡同起,渐渐有了默契依赖。
白日苏雅苦练左手剑,张缤伴着在庭院观看做着女工,夜里苏雅金针刺穴,张缤便寻来医书,研究利害。
张缤羡慕苏雅身手敏捷,似有飞天遁地之能,每每见她舞剑,总如一只小兔子一般藏身在庭廊之处,满目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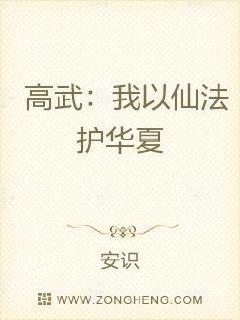
![[综漫]外挂是美食小游戏](/img/18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