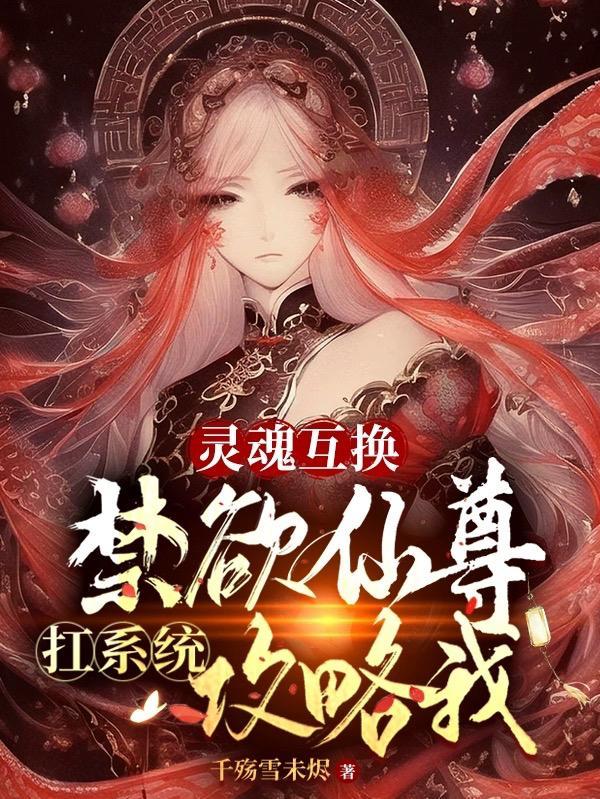爱上中文>殿下很勾人 > 第75章(第1页)
第75章(第1页)
似是乞求一般,她楚楚可怜地将茶盏直递到恭王唇边:“殿下……”
她素来被赞是戴家女儿里容貌最出挑的一个,眼下作出这般诱人情态,自信即便对方贵为皇子、见多识广,也将为之迷乱。
果然见恭王一双俊眼含情带笑,看向自己有意露出的一痕雪脯,就着她手里饮了一口,赞道:“美人柔荑,清茶添香。”
戴月盈心中大喜,正要就势坐进恭王怀里,忽见他脸色一凝——接着,蓦地喷出一口鲜血!
乐孟闻声,人还没转身,刀已出鞘。见萧彦吐血,立即断喝道:“茶水有问题!左右,拿人!”
戴月盈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外间那个方才对自己面色不善的高大侍卫已冲进来,拎小鸡一样将她拖到一边,随后接住摇摇欲坠的恭王:“殿下怎么了?!”
听见动静,原本刻意领着众人退至堂外的戴宏达忙赶过来。只见恭王双眉紧蹙,唇边带血,捂着心口瘫倒在椅上,全靠侍卫扶住。
戴宏达暗叫糟糕,面上更是惊诧惶恐:“这……二殿下这是怎么了?”
乐季半跪在地,扶住萧彦,转头恶狠狠质问:“倒要问问你们,给我家殿下喝了什么东西?!你们胆敢谋害皇子?!”
戴宏达饶是老练,也被他凶狠神态吓得话都不利索:“这、这这位都卫不可如此说话啊!明明我们与二殿下的饮食都是一样的,何来谋害之说?!”
一转眼看见缩在角落的戴月盈,立即惊讶道:“月盈?你怎地在此处?又怎作侍女打扮?!”
戴月盈此时全然愣住,戴宏达已痛心疾首道:“你这孩子,你恋慕二殿下,只管等伯伯为你提亲便是,你为何要作此轻薄装束,来此私会殿下?!”
屏风内诸人投来鄙薄眼光,戴月盈委屈至极:“月盈这么做,都是听从……”
不等她说完,戴宏达捂了眼睛:“快快整理衣衫,闺阁女儿这样成何体统!”
早有下人拿了罩衫来,戴月盈羞愧得哽咽难抬。
小舫
椅上的萧彦虚弱道:“本王近日奔驰劳累,原是无碍,只是方才闻见戴小姐身上香味,忽然心口发闷,谁想却吐出血来。”
戴宏达装模作样,听完下人的附耳禀报,愧疚道:“原来是月盈为接近殿下,在身上洒了迷情香粉,才致使殿下身体不适。”
早有府中医者过来为萧彦搭脉诊治,见状附和道:“是了,王爷本已疲累未愈,迷情香粉引起血脉紊乱,冲得心脉厷突,才会骤然吐血。”
戴月盈总算听出来,伯父是要将此事全然栽在自己头上。她立刻哭道:“不是的,香粉是伯母给我的,她让我……”
只是此时岂能再容她辩解,两个下人已架起她,拖下堂去。
萧彦只作没听见她的话,闭目叹道:“别苛责这个美人,只怪本王不中用,初初闻见香粉就吐了血,不但未亲美人芳泽,反倒吓坏了她。”
戴宏达听得明白,恭王话说得不失风流,其实意思是人他没碰过,因此不会负责。眼下人人见得,两位男女身上衣衫齐整,恭王连站都站不起来、别说能做别的,看来是无法赖上他。有此污点,以后戴月盈即便能进恭王府,也不可能当上正妃,这步棋还没开始便废了。
戴宏达暗道可惜,嘴上各种殷勤惭愧。恭王勉力在侍卫搀扶下起身,回下榻处休息。戴宏达哪还再敢挽留,跑前跑后相送,直到见马车在路头拐弯,这才恨恨跺脚:“这个没艳福的,白费咱们家一个女儿!”
一旁有子侄质疑:“来时看着好好的,他到底是真发病还是装病?”
戴宏达哼道:“医者搭过脉,他应该装不了。更何况给他的茶水里放了料,再闻见月盈身上的香粉,他一个血气方刚的皇子根本把持不住,做不了假;哎,想来是那迷情粉药力太猛,居然引出他的隐疾。”
一众子侄目瞪口呆:“伯父,原来真的是你安排月盈去勾引他?!”
戴宏达脸上挂不住:“那也是她自己愿意!若不是她运气不好,此时已成了恭王的人,日后便是王府正妃!老夫岂能害自家人?!”
有人心有余悸:“可恭王是在咱们家出了这事,虽然他今日没怪罪,难保以后圣上问责……”
戴宏达冷笑:“他不追究乃是明智。之前恭王差点死在北境,你可见圣上怪罪过谁么?!怕什么,咱们戴家站稳西南,只要贵妃和礼王殿下在,谁能把咱们怎么样!”
众人点头,三三两两回府,关了大门。
马车内,萧彦扶正头冠,对慌乱的乐孟摆手安抚:“不妨事,方才我咬破舌尖吐了点血,搭脉时自己按住神阙穴,自然脉象虚弱。”
乐孟略微安心,但见萧彦已是面红耳赤,猜测问道:“但是,那戴家女人的香粉,还是影响到您了吧?”
见萧彦默认,他反倒松了口气——看来并无大碍:“赶紧回去让顾先生诊治。”
车外乐季否决:“不可立即回去,否则衙内下人探得动静、告知戴家,殿下今日就白演一场;且上回林公子犯病,我见顾先生对此类症状……也没有什么好法子。还有,你出来。”
“——啊?”
乐孟起初不懂,再一看,萧彦软软靠在侧壁,已是星眸微淐、眼角泛红——尴尬得忙出了帘子,坐到车前乐季旁边:“殿下,那咱们去哪?”
萧彦浑身作烧,勉强思考片刻:“去水边,找个桥头艺舫。”
刚进南境便遇上驿站行刺,眼下不知有没有人暗中窥探行踪,安全起见,只能往热闹处去,待趁人不备浸在水中,或可熬过体内情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