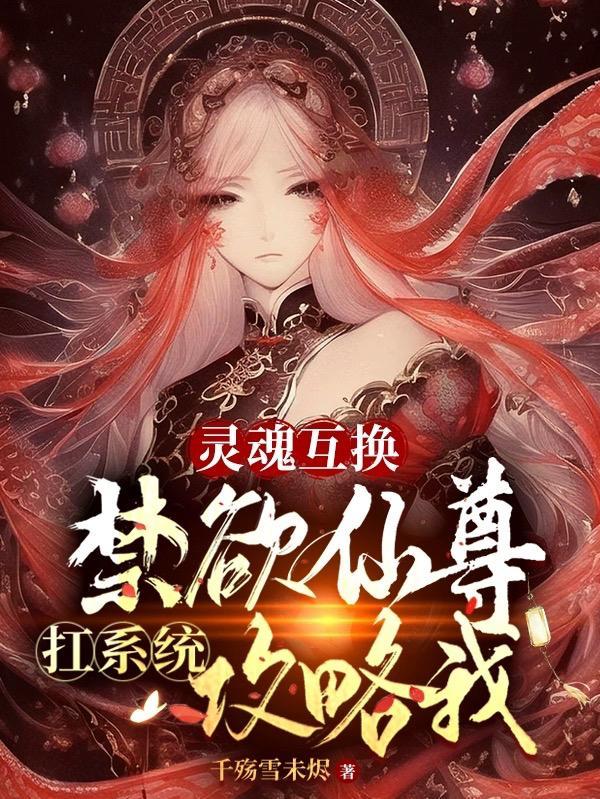爱上中文>殿下很勾人 > 第94章(第1页)
第94章(第1页)
——可乐季不谙水性。
说话间,打斗声自底舱传上甲板。
乐孟想前去援手,却不敢离开萧彦身边,忍住不动。
混乱中,听得舵手高喊:“转运了——!”
这是水手行话,乐孟略懂,抬头一看,漆黑夜色中,船帆已被吹向相反的一面——风向变了!
原本已完成缓慢掉头的大船渐渐停住,开始向港口相反的方向移动。
舵手竭力喊道:“大人,咱得赶紧收帆!”
但此时水手大多在底舱抢修,士兵也在底舱围着托达打成一团;甲板上的几个虽经验丰富,却都已老迈,不可能爬上桅杆。
乐孟急的冒火:“上来个人,去桅杆!”
“你去。”
萧彦及时发话道:“眼下天时地利都没有,人手也缺,你可统筹指挥,先解决紧要之事。”
乐孟迟疑:“可是船上还有刺客……”
一侧船舷传来“咚咚”
震响——江面已出现更多匪船。随着数量增加,水匪胆子也大,纷纷行至下风口,抛出钩绳钉在他们船舷,开始借助风向将大船往江心拉拽。原本架弩对峙的士兵不得不分出手,去砍钩绳,但钩绳外层淬过铁水,一时难以砍断。
乐孟握刀,恨不得跳上去把这帮耗子杀个干净;但此时必须立即收帆,减少风势。
萧彦指指椅边斜靠的佩剑,语气平淡:“只要船不沉,本王足以自保。”
自家主子临危不惧,举止自如,在这艘危机重重的船上犹如闲庭信步——乐孟紧绷到要断的神经忽然为之松缓:仿佛从前在北境,跟在他马后朝危城冲锋。
于是行礼后迅速朝桅杆冲去,走之前顺起一脚把愣神的顾行远推进房内。老水手在底下解开帆绳,乐孟猿猴一般三下两下攀上桅顶,顶着大风收帆。
底舱梯口却恰于此时翻上来一个精悍男子,豺狼般的灰眼睛往甲板一扫,窥见萧彦那边的防守破绽,挺刀直奔而去。
男子没穿上衣,胸前有个模糊的纹身,火把明暗中看不清,似是草原部落的样式——托达!
乐孟在高处看得分明,手上帆绳却才收到一半,若此时放手下去增援,船便将继续加速行向江心,那便更没希望获救——只得咬牙狠命加快手上动作,相信萧彦自己能抵挡一阵。
紧急情况太多,又缺统一指挥:从前这是乐季的责任。其他人都在船舷边与水匪相互射箭,无瑕顾及这边。
托达脚快,将身后追兵甩下,几乎畅通无阻,但甫一冲到房门口,一个木箱迎面飞来——当然砸不中他。
小木箱啪地掉在甲板上,药材银针洒落一地。
萧彦刚起身拔剑,就见顾行远扔出药箱,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挡在林文举身前,操起桌上烛台扑出去:“贼子!在下跟你拼了——”
“顾先生回来——”
萧彦完全没料到这位总是哭哭啼啼的怂货忽然起来拼命,不及阻拦。
顾行远不管对方手里明晃晃刀刃,抡起烛台往人脑门砸去。托达身量虽矮他一头有余,却轻松架刀一挡——烛台削为两段,刀刃直冲他咽喉而去——
林文举怔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只觉全身血液都瞬间凝固:“清圆——”
萧彦早已挺剑果断刺出,但隔着数步距离,难以及时救下。
刀刃在顾行远喉间划出道血印,却并未血光大起——托达收回力道后退,一记勾拳打在他肚腹,将他撇到一边:“啊,你是医者,草原人不杀医者。”
顾行远哪里经打,顿时捂住肚子倒在地上直吐胆汁,说不出话来。
萧彦趁机踏出房门,手中佩剑挽个剑花:“哥亥天青,你既然没忘记自己是草原人,何必装作小孩骗取同情?这才最为人不齿。不过如今也不会有人因你蒙羞——你的族人都已死绝。你给他们带去灾祸,最后却抛下他们逃跑。”
哥亥天青粗壮手臂上青筋条条暴起:“你是皇帝的儿子,可你连女人都杀,你们汉人才最刻毒!”
萧彦有意与他周旋拖延时间,嘲讽:“当初你劫绑本王,还不是为汉人做事?可怜你赔上全族性命,如今还不如汉人的一条狗。本王倒要点拨你:那个指使煽动你胆敢绑架皇子、与大魏作对的人,才是你真正的仇人。”
哥亥天青恨恨横刀,向前劈砍:“等杀了你,我再去找他!大魏皇子,咱们今天好好较量!”
“锵——”
眼见刀光近前,萧彦却忽地后退半步——斜刺里另一把刀精准刺来,接住哥亥攻势。
“你不配与他交手,”
乐季浑身滴水,但眼神如刀,全是蔑视:“怪物。”
“怪物”
这两字,比听到灭族还要令哥亥暴怒,顿时大吼一声,疯狂对乐季挥刀。
乐季已然看清他手里佩刀与自己一样,是王府侍卫制式,且刀刃血迹斑驳——王府侍卫人在刀在,刀若被夺敌手,说明人已遇害。大恨之下,乐季反而冷静,一边挥刀交战、引他远离萧彦,一边做手势令追来的侍卫形成合围。
林文举冲到顾行远身边,颤抖着想把他抱起来。顾行远连忙摆手,指指自己衣襟上的吐物:“脏,你快别碰。”
头顶乐孟忽然在桅杆上大声示警:“殿下站稳!”
屋内咣当一声,桌上茶盏滚落在地——船忽然大幅倾斜。
风帆
萧彦反应迅速,两步迈到两人旁边,佩剑向下扎进甲板,牢牢站稳。林文举会意,一手抓住顾行远、一手抱住萧彦云靴。
“哗——”
船身落回水面,浪花激荡,甲板剧烈晃动。没抓住身边固定物件的人难以控制地摔倒滚地。林文举到底力弱,终是脱手,翻滚之中不忘护住顾行远头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