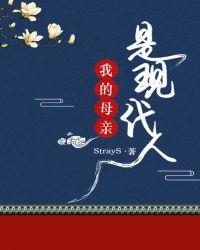爱上中文>魔尊x仙尊虐心 > 第23章(第1页)
第23章(第1页)
沈星河将他们的动作尽收眼底,却丝毫不觉得意外,像是早就知道会如何一般,走上前摸了摸那匹马的脑袋。那马被安抚下来,顺势将头在他手里蹭了蹭。
沈夜升这才想起他将马带来是用来讨好人的,眼前这副蔫头耷脑的样子实在说不过去,连忙解释道,“我们本来是想将它放在灵兽拉的车上带过来的,可它不肯被人碰。士兵被它踢了好几回,我们没办法,就让它自己走了。”
“士兵被踢了好几回”
,沈星河回过身看他,“你自幼跟我一起长大,自是知道我养的马是什么性子。你让士兵去牵它以后,是治好了他的伤,还是任由他退下去,再也不闻不问?”
沈夜升一时语塞,他怎么会这么口不择言。他大哥向来是连无关的人都要保护,要不然当年的事也不会演变成那般局面。他以为他大哥更在意他养大的马,可他大哥当年所做的一切,恰恰证明了他一生所求,怕是只有一句众生平等。
他知道这匹马被人碰就踢人的性子,士兵接到他的命令就必须服从。无论是马伤人,还是士兵受伤,归根结底都得怪到他头上。
沈夜升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找补的话,正犹豫间,就听到他大哥轻叹了一声,“你既任由他退下去,想必也说不出他姓甚名谁,伤在何处,如今又在哪里。”
“这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沈夜升似是怕他不信,急急忙忙回答,“我们刚找到这马时它不知怎的凶性大发,不曾伤人却不准任何人靠近它半步。”
说到这,他顿了顿,“我下了点命令让他们抓住它,当时上前的人和被踢的人是同一个,我听他们为抓到这匹马欢呼的时候,喊的是齐俊。”
沈夜升看了看在沈星河身边十分乖觉,跟凶性大发扯不上半点关系的马,小声道,“我怕它再发狂,就把人带了过来。齐俊现在应该跟那些老臣一样下榻在云梦城的客栈里。我若是没记错,他被踢的地方是手臂和大腿。”
到这里,他就不敢继续说下去了。他们从朝廷过来时,单是找来随身保护的修士和士兵就要比他们的人数多出十倍不止。他此番进九天炼只带了几个修士,不只是其他大臣年老力衰,更多的是想用苦肉计。
二十多年前,他大哥沈星河就证明了任何风霜刀剑都催不折他,阴谋诡计在他面前都派不上用场,能逼迫他的只有他人的性命,他们要想见他,除了身陷险境再没有旁的办法。
沈夜升想了想他来此的目的,咬了咬牙,尽可能的温和问道,“大哥您问这些是做什么?若是想给他治伤,大哥您何不跟我一起出了九天炼,亲自去看一看?那些老臣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沈星河的眉目不易察觉地低垂了几分,一双好看的眼睛向下看去,顾九思再清楚不过他这副模样的含义。他只有自我厌恶又无可奈何时才会这样。
上辈子的头两年里,偶尔他从沈星河的床榻下来,就会看见沈星河的这副模样。
那时沈星河给他化劫的次数已经数不过来,他们俩便是第一回生疏,到后来也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更何况沈星河向来是不会耍手段折磨人的,他们两人最开始还能说只是纯粹地被劫数所迫,到往后却谁也说不出口了。
顾九思是真的屈居人下,可他也确实避开了天道给他降下的屈居多人的劫数,借着双修提升了道行不说,又实实在在地得到沈星河的庇护。就连屈居人下这一点,也因对方是沈星河,变成了一件不能说不好的坏事。
沈星河跟他的心境却又不同。
沈星河最开始是被他下了意欢草,后来是因为他那既是君子又像狗的心性,不得不帮他化劫。可当沈星河从不得不里体会到其他感觉时,他就会因为无法说服自己是被迫的,陷入一种自我厌恶里。
这种自我厌恶本有办法解决,要么他不再找沈星河,要么沈星河杀了他。
他们两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答应天道给他降下的劫数,沈星河成神失败后都不能立马杀了他,再往后就更不可能。
顾九思始终不懂沈星河成神失败后没有立马杀了他的理由,却还是明白,他成了沈星河的无可奈何。
眼前的沈夜升,同样也是沈星河的无可奈何,唯一的区别是顾九思几乎无可解,沈夜升则是还没到该解的时候。沈星河的娘亲还有四年才能转世投胎,在她降生于世之前,沈星河绝不肯让他死。
“我跟你们说过,日后再见会如何。”
沈星河给马施了一个清洁咒,随手理了理它重新柔顺的毛发,“可你们总听不进去。我宽厚待你们时,你们不以为意。我手段强硬些,你们又跪在我脚下痛哭。”
“沈夜升”
,沈星河冷漠地质问道,“你们还能带多少稚儿到我面前自尽?当年那些撞柱给我看的大臣,如今还剩下多少?我把你们的命当命,是让你们将它当儿戏,告诉我人命确实轻贱不值一提的?”
“可我们真的知错了”
,沈夜升也顾不得还有其他人在场,连忙哀求道,“我们就是听进去了,才二十年都不敢来见您。可您这次愿意用云梦城的城主封石,不就是代表您松口了吗?我们不远万里的过来,您真的连见我们一面都不肯吗?”
他满口都是哀求,却句句都是威逼,顾九思有些听不下去。哪怕他不能在这时杀了沈夜升,也该把他从这里丢出去。他刚要动手,沈星河就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一般,转过头不轻不淡地看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