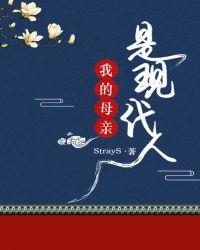爱上中文>满朝文武爱上我 > 第86章 构害入狱(第1页)
第86章 构害入狱(第1页)
第二日起来,顾望之只觉得自己头疼的紧,她虽酒量不佳,可也甚少像如今这般宿醉,就连洗漱穿衣都是由着锦瑟摆弄,自个儿迷迷糊糊地便被送上了马车。
直至进了宫,鸿蒙时微冷的晨风才将她吹得清醒了几分,佩了牙牌,又听鸿胪寺唱入班,几番流程下来,顾望之的困意也彻底消散了去。
从六品的起居舍人,在满朝的达官显贵面前自然也不算什么,不过是沾着太子的福,方能在站个中间的位置。
本是在议今年税收一事,一部分官员要求减税,缓和民生,一部分官员又持反对意见,说今年国库空虚,若再缩减税收只怕不妥,两派相持不下,官家不好决策,便说以容后再议来托委。
“众卿可还有本启奏?”
赫连珽现下身子不大好,早起又受了点寒风,如今愈有些头疼了。
“臣有本启奏,”
大理寺卿常盛上前道,“臣弹劾吏部员外郎顾望之,掩袖工馋、代拆代行,利用吏部之位,贪污受贿、以图祸乱朝纲!”
顾望之被这突然起来的一番诬告弄得有些蒙,她行事素来小心谨慎,别说是贪污受贿,就是与朝中诸位大臣都甚少有所往来,又怎的被扣上了这么大一顶帽子。
“常大人,说话可要讲究证据,”
赫连璟沉了眼眸,冷冷道,“诬告朝中官员,也是要定罪的。”
常盛身居要位多年,又怎会轻易怕了赫连璟话中的威胁之意,只拱手上前道,“顾望之在协办徐州知府贪污一案时,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于当时尚任同知的李泉,将地方上报其倒卖官盐、克扣粮税一事的证据销毁,在张庆芝获罪后,立即以贤能堪用之名扶李泉上位,意图将徐州操控于他一人之手。臣手中,有李泉贪赃枉法的罪证,及两人的书信往来,请陛下亲阅!”
一旁的太监授意,连忙将常盛手中的奏章呈了上来,他审阅良久,忽而唤了顾望之上前,将奏章扔在她面前,震怒道,“你自己看看!”
若非赫连璟力排众议极力推举,他本是不想重用顾望之的,一个毫无根基的少年,便是有些才华又如何,连心思都定不明白,如何能堪以大用。
顾望之心中一惊,指尖有些微微颤地拾起地上的奏章,其中记载的李泉种种罪证皆是证据确凿,辩无可辩。可她根本不曾同李泉有任何往来,这书信上又确实是她的字迹,加上先前朝堂之上,自己受赫连玦所逼,又确实举荐了李泉任徐州知州,种种下来,几乎是坐实了她徇私舞弊之名。
对,赫连玦!顾望之猛然惊醒过来,难怪她先前查不到关于李泉的任何罪证,她原以为赫连玦是为了扶李泉上位将其暗地里所做的苟且之事都摸了去,原来他一直将其握在手中只等着此时来给她重重一击。
至于书信,赫连玦手下奇才辈出,想来能寻出一个能模仿她字迹的也不算什么天大的难事。
原来,他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自己。顾望之闭眼深吸了一口气,冷汗几乎浸湿了朝服,是她自作聪明,以为一招瞒天过海能够扶了蔡京上位,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她的把戏怕是在赫连玦眼中不过是跳梁小丑,可笑至极。
顾望之瞬间红了眼眶,她不甘心,自己步步为营,明明只差一步就可以扭转徐州局势,可一子之错便满盘皆输。
“臣并未做过任何贪污受贿之事,陛下可彻查臣名下所有资产和徐州一案卷宗,”
顾望之挺直了脊梁,定定地瞧着端坐在帝位之上的赫连珽,“这书信,乃是有人刻意模仿的臣的笔记,蓄图陷害。臣恳请陛下明察。”
顾望之一下一下地在大殿之上叩,寒窗苦读数十载,她决不能在此刻认输。
朝野上下,百官伫立,作壁上观者,唏嘘喟叹者,冷眼嘲弄者,便静静地瞧着这位风光无限的少年状元如何跌落神坛。
“徐州一案儿臣是同顾员外一同处理,若他真有不轨之心,儿臣又怎会毫不知情,”
赫连璟上前拱手道,“儿臣恳请父皇给儿臣一个机会,让儿臣彻查此事。”
“臣相信以顾大人的秉性,绝不会作出此等有害纲之事,”
苏既白上前,叩道,“臣恳请陛下彻查。”
“满朝皆知,顾望之是太子殿下的人,此事若是交由太子殿下查,怕是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常盛上前,冷冷瞧着两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