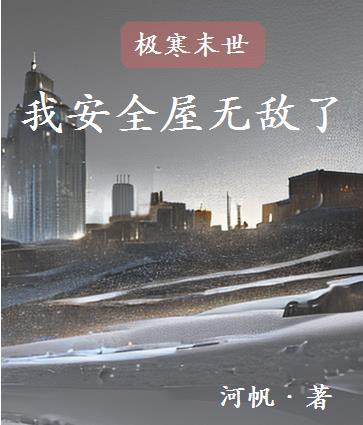爱上中文>九锡禅杖 > 005织经司(第1页)
005织经司(第1页)
广陵城,府衙后宅。
偏厅中两人对面而坐,桌上放着一张棋盘,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呈现出纠缠不休难分难解的格局。
居北那人一袭长衫,白面短须,神态温润。
他凝望着棋盘上的局势,眼下他的黑棋看似占据上风,但两个边角处皆有隐患,稍有不慎就会让对方盘活大龙。
这盘棋从上午进行到现在,他落子的间隔越来越长,频繁进入长考的状态。
“难办,很难办。”
他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封堵对方的飞子,要么稳固自己的中腹,看起来各有好坏因而难以取舍。
“府尊大人,您今儿这棋相较往日可要慎重许多。”
棋盘对面坐着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男人,略显富态的面庞让他多了几分憨厚气质。
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在外人面前都是这副模样,行商数十年极少与人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广陵府地界内,6通这个名字即便不算家喻户晓,也能称得上声名远播,而且还是偏正面的评价居多。
6通这段时间心情大起大落,独子6沉第一次出远门,他明面上笑呵呵地送行,内心自然无比关切。先前接到6沉病重的消息,他险些晕厥过去,还好没多久又收到6沉康复的喜报,他那颗悬着的心才平安落地。
本来他今天要亲自出城迎接6沉,谁知还没出门便被面前的广陵知府詹徽请到此处,拉着他下了一盘极其漫长的棋。
詹徽端起手边的茶盏饮了一口,感慨道:“数月未见,你的棋艺又精进了。”
6通笑道:“府尊这话可是折煞我了。单论棋艺,府尊便是只花一半精力都能杀得我溃不成军。平日里难得碰到府尊心思恍惚的机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赢一局。”
这句话意味深长。
詹徽放下茶盏,没有去看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抬眼望着直到此刻依然平静的6通,沉默良久之后终究出一声轻叹。
6家虽然不是世家望族,但几代人数十年来在江北之地打拼,根基委实不弱。
不说旁的,詹徽履任此地知府后,6家鞍前马后提供了不少支持,因此他在去年吏部的考评中如愿得到一个“中上”
的批语。
不出意外的话,过两年他就可以回到京城,品级也能再往上提一个台阶。
一念及此,詹徽不禁压低声音说道:“我本以为你今日不会来。”
6通摇头道:“府尊这是哪里话?这些年如果没有府尊的照拂,6家的生意也没那么好做。犬子确是今日返回广陵,但与府尊邀约相比,于我而言根本不需要犹豫。”
詹徽迟疑片刻,最终还是坦白道:“按说我不该故意欺瞒于你,但这件事是织经司的安排,你应该知道那些人的厉害,我只能将你留在府中——”
6通心中一暖,打断他后面的话:“府尊,无妨。”
便在这时,一名三旬男子缓步走进偏厅。
其人身段颀长,相貌英挺,周身散着冷峻的气质。
詹徽与6通同时起身,前者介绍道:“这位是苏云青苏大人,现任织经司淮州司检校,负责淮州境内的一应事务。”
6通面露惊讶,旋即恭敬地行礼道:“草民6通,见过苏大人。”
苏云青走到近前,上下打量了6通一番,淡淡道:“苏某时常听闻6员外的善举,很想亲眼见见,只可惜一直以来缘悭一面。”
6通微微垂道:“苏大人言重了,草民不过是区区一介商贾,委实不值一提。”
苏云青似笑非笑地道:“6员外何必自谦?苏某的好奇并非虚言,这些年查办过不少勾连敌国的细作,很少有人能如6员外这般尽得一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