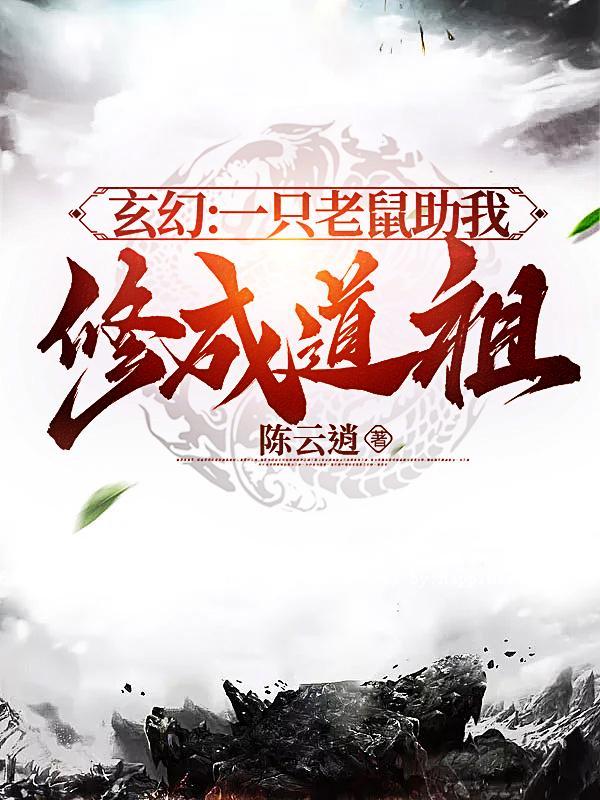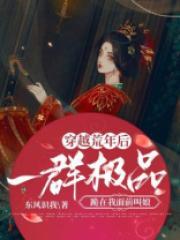爱上中文>朕真的不务正业笔趣阁 > 第883章 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第3页)
第883章 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第3页)
范应期的案子是海瑞办的,海瑞都只是追欠了赃款、罢免职位、褫夺官身、功名,没有进一步的威罚,让范应期改名,就是日后这人的事儿,不必再连累到王家屏身上了。
朱翊钧对范应期非常可惜,就像他一直念叨刘汉儒这个循吏,刘汉儒很能干,他把三都澳私市经营的极好,若不是碰了阿片、私市这两个不能碰的红线,不会坐罪论斩。
相比较死不悔改的林烃,刘汉儒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他还是为了升转,什么都做了,那国法就留不得他了。
“臣谢陛下隆恩。”
王崇古选择了谢恩,这毫无疑问是宽宥,给王家屏解决了后顾之忧。
朱翊钧拿出了一本奏疏,面色十分犹豫的说道:“申时行上奏说要加钞关的关税,从13%加到24%,增加11%,大明腹地课税不变,这样就形成了内外的税差,促进大明内部市场的形成。”
王希元要让天下势要豪右立字据站台,斥责逆党行为,形成投献事实;
而申时行则是要加关税,说的是为了大明内需建设,但其实就是为了威罚江南选贡案,他在奏疏里把这一目的说的再清楚不过。
因为加这11%的关税,这帮势要豪右宁愿加价降低销量、降点利润继续往外卖,也不会太愿意供应内部。
这里面涉及到了极其复杂的成本问题,税只是大明国内成本之一。
那些个把持着地方衙门的地头蛇们,恨不得粪车过道,都要喝一口才罢休,这种隐性成本、地方税务、风险,可比这11%的税高得多得多。
池州府劫船案,刚刚问斩了一群人。
王崇古倒是颇为赞同的说道:“臣倒是赞同,关税不收,如何建设海关呢?海防巡检司要钱,水师也要钱,维护近海贸易的安全,是需要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林烃把星图和针图,交给了海上的亡命之徒,大明剿灭海寇变得更加困难了,为了不至于近海贸易的安全形势彻底崩溃,需要更多的白银,建设大明水师和海防巡检,这让加税变得合理了起来。
至于申时行说的建设大明国内需求的效果,王崇古也不是特别看好。
“银子暂时还够用,更多的银子在市场里,反而有利于开海大事。”
朱翊钧的倾向是不加。
关税就是个抽血泵,只要开动就会吸工坊的血,更多的银子留在市场里,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形成。
横向转移支付,是一种平衡内地沿海展不均衡的手段,不是要把沿海的流动性抽干。
13%的税赋,不多不少。
“臣以为陛下所言有理,那山东巡抚宋应昌说的也是有几分道理的,是这些反贼选择了江南,而不是江南百姓选择了反贼,江南也不都是反贼。”
张居正觉得完全没必要加税,大明是制造国,原材料进口国,高昂的关税,反而不利于生产。
关税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持续推高关税,还不如不开海,直接禁海,闭关锁国。
“那就暂时不加,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加。”
朱翊钧选择了暂时不加关税。
既然以西土城为的势要豪右上了斥表,朱翊钧没有进一步的追击,不再扩大打击范围。
张居正讲了一件这十三天时间里,生的一件怪事,五大市舶司远洋商行的商总、船东们布了联合声明,斥责逆党。
一些个开海之后富起来,没在册的富商巨贾,有些不满,凭什么只有之前的势要豪右、乡贤缙绅才有资格上斥表?他们也可以表态,也可以爱大明,也可以忠诚!
不在册的富商巨贾就不可以忠诚了吗?
以五大市舶司为的富商巨贾们,开始表联合声明,之所以朝廷没有要求,富商巨贾也要刊登联合声明,是因为南衙选贡案这把大火烧的太大了,这些富商巨贾们生怕火烧到自己身上。
“陛下,徐州知府刘顺之第四次请见了。”
一个小黄门见皇帝、元辅、次辅谈完了正事,见缝插针的奏闻了刘顺之求见。
“宣。”
徐州知府刘顺之终于见到了大明皇帝。
“臣刘顺之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顺之恭敬见礼,他这一趟真的不容易,终于在桃山驿行宫见到了皇帝陛下。
“免礼,坐下说话,之前江南选贡案有些复杂,朕就偷了几天懒。”
朱翊钧笑着示意刘顺之坐下说话,顺便解释了下这几天他在等什么。
刘顺之是举人出身,也没有恩科进士,这是他第二次任职徐州知府,他第一次是在万历元年,干了三年就离任去了琼州,是皇帝来到了徐州,看着这地方一塌糊涂,又把非常被徐州人认可的刘顺之调了回来。
徐州地方,有点邪性。
在地方官里,知府就是一道坎,有些人兜兜转转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