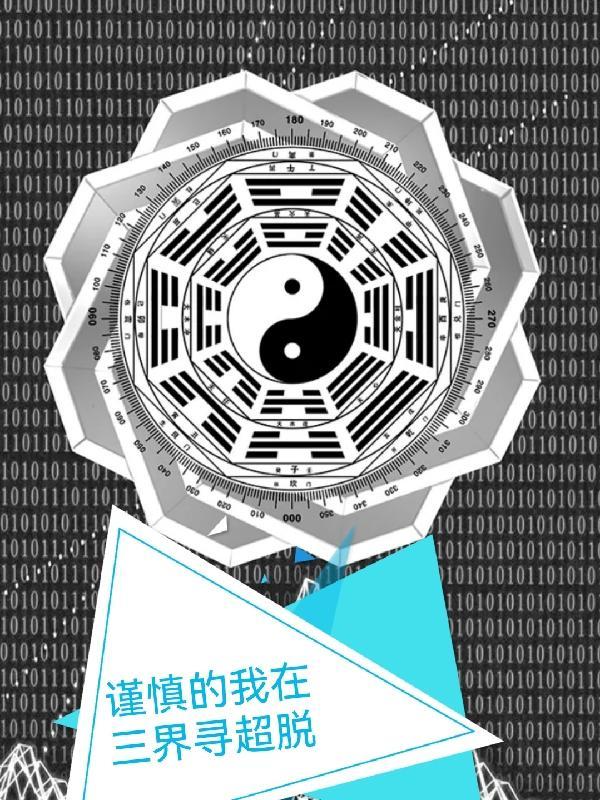爱上中文>却实在美丽小 > 第45章(第1页)
第45章(第1页)
>
男子抱着他,安慰似的捏了几下,又轻轻描摹他的耳廓:“娇娇。”
谢玉神色一滞,听他哄:“娇娇,好眠。”
。
再次将人哄睡下,霍寒才松上一口气,目光流转,渐渐停在那一箱情书上。
他不自觉想起之前,自己和谢玉表白的场景。
那时他还在盛林书院,一年一度的马术大赛上,谢玉甩了他半圈拿了第一。
但他走过去恭喜的时候,少年却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开心,甚至一把将奖品塞进了他手里:“我不要了,你明明可以赢,不必如此让我。”
“可我喜欢你。”
霍寒争辩:“让着一些,不是应该的吗?”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表白。
那段时间,书院盛传谢玉好男风,情窦初开的少年难免觉得新奇,很多人都在拿谢玉开玩笑。
说的多了,就连谢玉也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难免发火:“够了!霍寒!世家子里好男风的少还是京城的小倌馆少?这么逗弄我有趣吗?!”
“你若是觉得新奇,大可以随意寻个南风馆一探究竟,何必招惹……”
“不是新奇。”
他打断谢玉,认真说:“我觊觎你,我喜欢你,我想要你。”
“……只有你。”
春意正好,风吹旗动,谢玉没同意也没反对,径直转身远离。
他也没敢再找过人。
一旬之后,玉儿却主动把他赌在了膳堂边的小巷里,主动吻他,扬言要娶他做男妻。
他当时在笑:“古往今来,世间无一名男子,愿意娶另一名男子为正妻,皆言荒唐至极。”
“是吗?”
谢玉回:“那我便是开先例者了。”
那时候,十九岁的谢玉无权无势,鲜衣怒马,张扬的像是傲雪而立的梅花。
现在,二十七岁的谢玉一人之下,如履薄冰,脆弱的像是一碰就碎的瓷器。
。
深宫,盛长宁的火气依旧没有消。
虽说他不该有这种反应,但一想到谢玉不再受他控制,不再将他当成唯一,就会忍不住心慌。
他时常做噩梦,这种侵骨蚀心的感觉,一月以来,几乎掏空了他所有的安全感。
以至于英国公入宫告状,都被他乱棍打了出去。
怎么能……
怎么能呢?
玉儿从南梁逃回来的那段时间,满朝文武都想他死,只有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救……
玉儿以前……很久以前……明明对他很好的……
哗啦——
盛长宁不知哪儿来的火,竟是搁下手中狼毫,一把掀翻了面前铺满奏折的御案——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