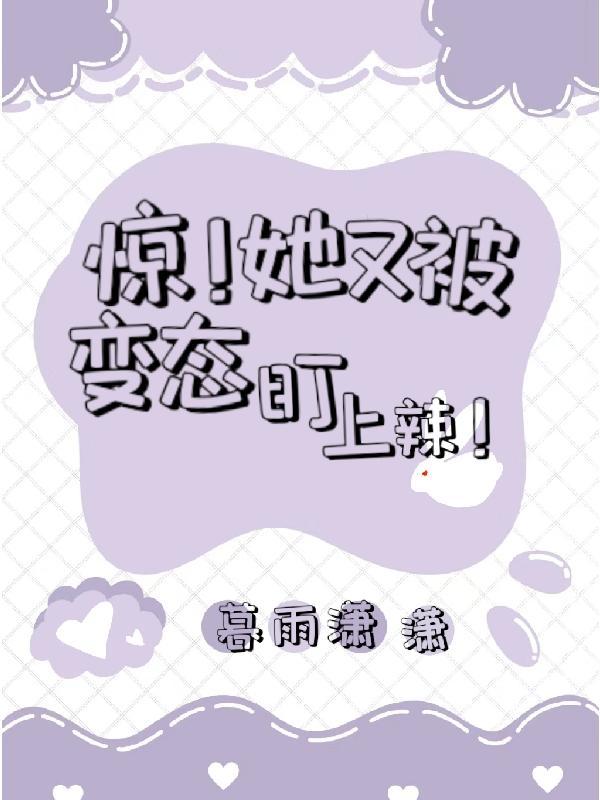爱上中文>濯英泉 > 第24章(第2页)
第24章(第2页)
“你倒是会伤人的心,我待他难道是假意?他唤我一声叔母,我把他当亲子,在我眼里,他同清微长年是没分别的。”
寒复无意再辩此事,只道:“夫人,你莫要再固执,此事绝无更改!”
颜夫人怒气上涌,“我明日到许家去!我阿姊可不会害她女儿!”
“夫人!”
寒复撑住头,哀声道:“夫人若是担忧兰姿将来委屈,我会再去告诫三郎,他是最知进退的人,不会叫你失望的。”
“许家是去不得的,此事不宜再闹了,再闹,必然生芥蒂,又是何苦?”
颜夫人冷笑着道:“你说是为三郎好,那你可曾问过他,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是你要给他一个得力的妻族,他自己真的想要吗?你别太自以为是!”
寒复不说话了。
颜夫人又道:“他只听你的,你现在就去,告诉他,叫他由着自己的心选。”
寒复不动。
颜夫人急了,“你怎么不去?不是讲一定听我的?”
寒复还是不动,而且也不作声。
颜夫人喘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君子一言九鼎,你难道是小人不成,才说过的话也敢忘!”
寒复道:“若为此事,我甘愿食言。”
颜夫人抓起几上玉盏狠掷过去。
钟浴存了尽快离开的心思,所以自寒宅归来之后,万事不理,只一心默书。
二月底,钟浴默完了书,托人转送许韧。
她再一次清点起行装来。
颜夫人每日都会送帖到姚宅。
钟浴一次也没有应过。
二月的最后一天,颜夫人亲临姚宅。
钟浴无奈只能出面接待。
见了面,颜夫人抓住钟浴的两只手,无论如何不肯放。
“听闻你要走?”
钟浴笑着说是,“我有些要紧事得做,不能再拖了。”
颜夫人就问:“什么事呢?”
又说,“你告诉我,只要告诉了我,无论什么事,我都一定给你办,我不是妄言。”
钟浴道:“夫人的好意,我先谢过,只是我这件事,旁人无法代劳的。”
“究竟什么事呢?”
“我要去父亲的坟前拜祭。早该去的,只是一直有事,这才耽搁至今。”
钟浴提及她早逝的父亲,颜夫人听了,难免心中作痛。
这可怜的女孩子。
她的真情,等不及试探,顷刻间全倒出来。
“好孩子,你同我讲,可是三郎伤了你的心,所以你才要走?”
不等钟浴回应,她又讲:“你错怪了他,他实在是不得已,他也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