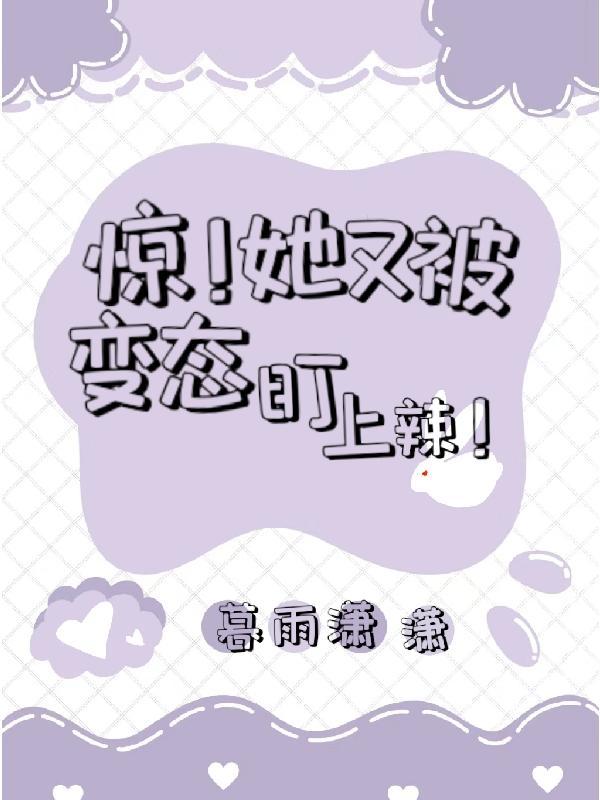爱上中文>手足无错什么意思 > 第64章(第1页)
第64章(第1页)
艺海饭店观景台的咖啡厅,楚耀南同惠子临江而坐,喝着咖啡。
楚耀南气度潇洒,靠了座椅,端着咖啡轻轻搅拌,眼眸就落在咖啡上一层淡淡的奶沫上。
那白色绮丽的泡沫渐渐的消融,化入混沌的浆水中。
“怎么,还难过呢?”
惠子问,带着善解人意的浅笑,“女人的触觉最敏感,你的眼睛会说话。”
楚耀南猛地抬眼,又避开她,落荒而逃般,自我解嘲地望着江面一笑说:“笑话,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有什么难过?”
惠子放一块儿糖进咖啡,那动作轻盈,侧头笑笑说:“老同学,你我就不必转弯抹角了,我有个事求你帮忙。”
“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
楚耀南说。
“你肯定能做到,就看楚大少愿意不愿意做。”
“说来听听。”
楚耀南说,“我不会事先答应任何事,条件讲好之前。”
“条件?呵呵,你该不会让我以身相许吧?”
惠子咯咯的笑,露出几分妩媚。
楚耀南唇角一牵,一抹骄傲的笑意挑起,那迷人的眼眸半含温情道:“我对有夫之妇,没兴趣。”
惠子脸上的笑意顿时收敛,尴尬的笑笑侧头去扶被风吹散的鬓发,楚耀南呵呵的大笑靠去椅背说:“逗你呢,别做真。”
惠子娇嗔地望着他,含着莫名的笑,许久才说:“直说了吧。我的小叔子,开了家株式会社,就是你们的洋行。现在急需一笔大款子周转,时间不多,一个月,就一个月在账面里入账,银行放一个月,再拿出来。百分之六的利息,还划算吧?”
楚耀南随口问:“你需要多少钱?”
“五千万。”
惠子说,“一个月,就净赚三百万,还划算吧?”
楚耀南心一动,但沉着说:“可惜,我没钱。”
“秦氏商会那么多账目往来,如今还是走你的楚大少的手吧?再过个一年半载,是否还能沾你的手就不一定。这笔钱,我本是可以去别的地方筹措,只是一来麻烦,二来,真心想照顾老同学你。darcy呀,我都为你着急。第一桶金,总是要得的,才有创业可言。一个月的功夫,三百万,不过倒手,神不知,鬼不觉的。”
楚耀南的眼神开始游离在江面上,渡轮往来,长鸣而去,江面拖出长长的白浪,向江边涌来。
“不行,蓝帮的规矩严,我还要命呢。”
楚耀南紧紧捏了咖啡杯,手背暴露出青色脉络。
“我会害你吗?此事,你知我知,一个月后,账款直接进你国外的银行账户。darcy。”
楚耀南茫然的目光望着江面,喃喃说:“容我再想想。”
楚耀南起身,惠子也礼貌地提了裙子起身,楚耀南绅士的走到她身后为她搬开椅子,惠子才想起来说:“让我打听的那个人,我问到了。在东北奉天,地址,在这里。”
惠子从手包里取出一个纸片说:“想不到事隔这么久,还有人对小丹桂和沈焯的传奇如此痴迷,不远千里要看他们的传人。”
楚耀南腼腆的说:“是,我的一位老师,尤为崇拜沈将军,说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挽救了中国。所以,我自小就崇拜他。”
“可惜,可惜,东北那家沈家传人,都是沈焯将军和原配夫人及两位小妾的子女。小丹桂,听说她生的儿子在大狱里就冻死了,冻僵了,可惜可怜。金戈铁马,烈焰红颜,这样的故事才凄美。”
楚耀南听惠子娓娓道来,竟然忘记两人立在餐桌旁,就那么站在江边,引来无数人侧目观望。
楚耀南立在父亲的书房,书房内还有费师爷和秦溶。
“父亲,可否听耀南一句劝,五千万,扔下去补青道堂无异于将钱扔进外滩江水里,打个水漂什么都不剩下。”
楚耀南耸耸肩,瘪瘪嘴,无可奈何的样子道,“五千万,父亲可以用他重新建立个蓝帮分舵给二弟名下,即便另立门户,这笔钱数目可观。但是,投资青道堂后患无穷,今天这窟窿是我们查见的,有多少漏帐隐患是我们尚不可见的?父亲,三思,让青道堂,自生自灭吧。秦氏不是慈善堂。”
楚耀南慷慨陈词,秦溶拳头攥得嘎嘎响,只差冲去狠狠揍楚耀南一拳头,打花他那张趾高气扬漂亮的脸蛋,那迷人的笑容都带了嘲弄。
“耀南,秦氏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
秦老大沉吟片刻出言道,惊得师爷一个战栗,张张嘴正要圆场,楚耀南毫不犹豫从腰间摸出勃朗宁小手枪,众人惊愕的目光下只枪口一转掉转向自己,拍到父亲桌案上决绝道:“杀了耀南吧。日后青道堂那烂摊子出状况,也是我责无旁贷,死路一条,与其那时,父亲何不现在就处死耀南?”
楚耀南深抿薄唇,痛苦道:“父亲,是您昔日教给耀南,做买卖,在商言商。”
指指头脑说:“这里的东西,不能掺杂进去。”
秦老大不语,只是好奇地打量楚耀南,目光凝成一线,如豹螭般凶光毕露。啪的一拍桌案骂:“你是要挟你老子吗?”
不待楚耀南答话,挥手一掌狠狠抽在楚耀南面颊上。
“南少!”
费师爷惊叫一声去劝。楚耀南唇角已渗出血渍,满口血腥,也不敢去擦,痛苦的望了父亲道:“儿子,明白了。”
秦老大沉口气,绕过书案,从袖口里摸出条帕子,为楚耀南擦拭唇角说:“爹也是心急,知道你近日忙碌,又跳出青道堂这桩烦心事。爹何尝不知其中的麻烦,只是,青道堂,对爹,对你二弟,都意义非常。那是,溶儿的家,破家,值万贯。蒋堂主也是我的恩人,你知道,知恩图报,我就喜欢你二弟这点憨实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