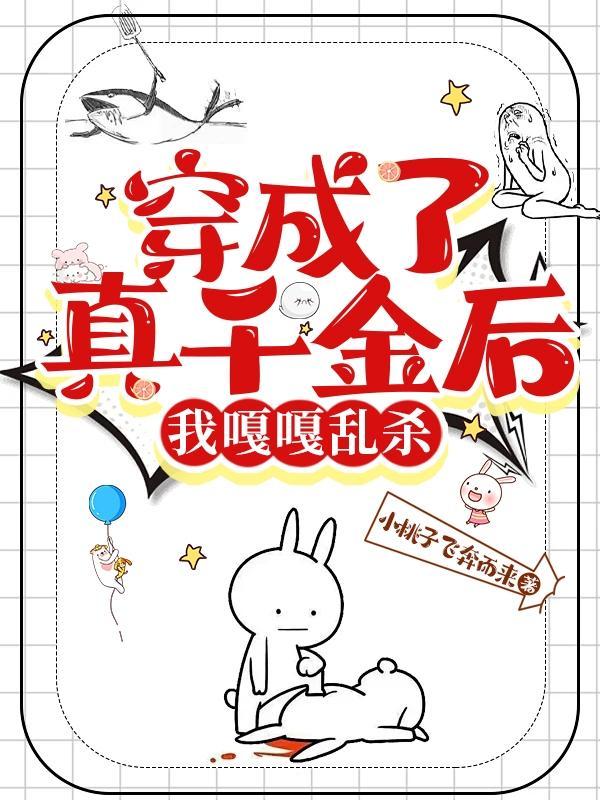爱上中文>团宠反派小郡主 星杳杳 > 第343章 若你记起前世(第2页)
第343章 若你记起前世(第2页)
而竺昙云诃下的毒,却是一点一点加重对中毒人的折磨。
“放心,你不会死得太过简单的。”
竺昙云诃这时的话验证了她的猜想,她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望着地上那狼狈的人。
阿鹿桓钺的手死死抠进了泥里,声音宛如恶鬼悲鸣:“你!你、杀……孽……”
牛头不对马嘴的几个字,又换来一声轻笑。
佛子伸出手来,颇有兴味地翻转了一下,缠在虎口处的佛珠内敛光滑。
“既然师兄非要以身为棋,那我便将这局杀得更精彩一些。更何况……”
他顿了顿。
“我稳坐佛塔,手中执的是伞而非刀;我袈裟洁净,血渍未沾染分毫,何谈杀孽?只有慈——悲。”
最后两个字一字一顿的,阿鹿桓钺却只在乎一点。
“师……兄?”
“带着你的疑问,在痛苦中死去吧。”
竺昙云诃单手作礼,“阿弥陀佛。”
是的,阿鹿桓钺不会知道,曾经他的儿子才是佛子的最佳人选,但凡他存有一丝人性,便不至于父子相残;他所想要的大业,或许也无需为了作为傀儡而毒了另一位佛子的眼睛,留下仇恨。
他抬起手向后摆了摆,立即便有人前来将苟延残喘的阿鹿桓钺带走。
满满压制住这短时间内对他生出的畏惧之心,着急地想起身提醒他云迦怕是拖不起了,却失力摔回去好几次。
“佛、佛子,云迦他等不起了。”
“郡主,你起初来西域是为了什么,还记得吗?”
他却忽然反问。
“啊?”
满满愣了一下,也下意识地跟着他的问题去想,自己起初来西域是为了……给无难寻药。
他从袖中摸出一个瓷瓶,单手将塞子松了松。
即使是雨夜,满满也嗅到了那抹熟悉的药香,脱口而出:
“这是阿鹿桓钺密室里的药?!”
“正是。”
竺昙云诃薄唇轻启,将药瓶递出,说的却是残忍的话:
“你也是医者,想必知道拖到此时,师兄的情况已不容乐观,但这个药却能让他起死回生。
可此药只有一颗,那么郡主,你是要用它救师兄呢?还是要将它带回大裕,去救你的‘心上人’呢?”
满满顿时震惊地抬头。
她的喉间仿佛有个石头堵着,吞不下去,吐不出来,脑海中又仿佛有无数只蜘蛛吐了丝,缠得乱七八糟。
“我……”
她的嘴无助地张了张,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竺昙云诃的表情冷了下来,缓缓道:
“殷满满,若你记起前世,会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