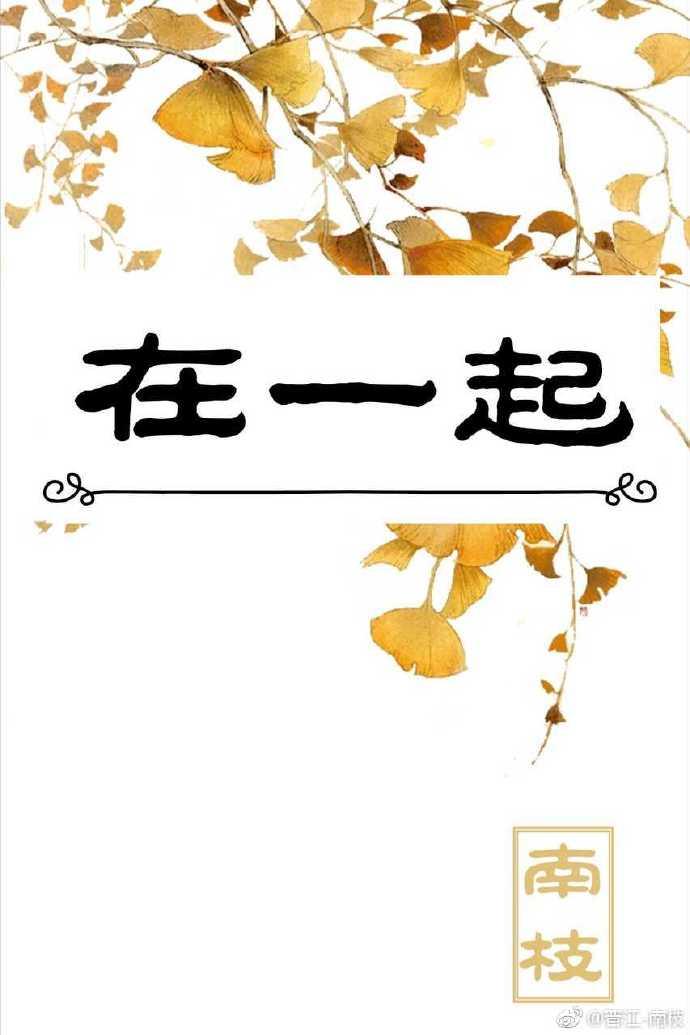爱上中文>与君执山河 以北yibei > 第三十四章 国丧(第2页)
第三十四章 国丧(第2页)
程纾禾看着他,敢怒不敢言,负气哼了一声,又拉被子蒙脸躺下了。
司徒策无奈叹了口气,想了想方才和声道:“你好好休息,我明日再来看你。”
“陛下日理万机,不敢打扰,不必每日都过来。”
她躲在被子里瓮声瓮气道。
司徒策瞬间被气笑了,想了想道:“朕的皇后病了,朕焉有不来的道理?”
闻言,程纾禾立即从被子里钻出来,又急又恼,口不择言道:“司徒策,做人要讲诚信!”
“安心养病。”
司徒策说着,也不管程纾禾是何表情,起身走了,留下程纾禾在身后骂骂咧咧。
傅清初在一旁看着,劝谁都不是。司徒策路过她时,牵着她的手走了。
“你把傅司闺留下!”
程纾禾在身后气急败坏道。
“皇后病了就好生歇息吧,今日就不让她在这儿打扰你了。”
司徒策笑道。
“司徒策!”
程纾禾气得不行,却又不敢骂得太过分,憋了半方才吼道,“你无赖!”
司徒策牵着傅清初往外走,恍若未闻。傅清初频频回头,想要挣开他的手,司徒策却越拉得紧。
“她本来就生着病,我还是留在此处照顾她吧。”
傅清初皱眉担忧道。
“太医都说没事,你就别操心了。”
司徒策淡笑道,“这段时间你也累了,今日就好好歇歇吧。”
见他神色疲倦,傅清初也没有再说什么。
……
服侍司徒策喝药躺下后,傅清初方才洗漱上床。刚躺下,就被司徒策搂了过去。
她伸手帮他掖好身后的被子,柔声道:“睡吧。”
司徒策叹了口气,“我是不是真的言而无信,忘恩负义啊?”
闻言,傅清初不禁失笑,“她在气头上的话你也信?”
“从她的角度来说,似乎确实如此。”
司徒策想了想道。
“但做事要顾全大局,先帝尸骨未寒,你就急着将他外贬的官员调回来,别人该说你不孝了。”
傅清初和声宽慰道,“明儿我去给她解释,她是明事理的……”
“你以为我没给她说过?但是人家说的什么?徐轸已经忠于我了,贬谪徐敬光便是,与徐轸有什么关系?”
说到司徒策无奈又好笑,“到底是心疼心上人。”
闻言,傅清初亦是笑了起来,“营州苦寒,尤其是入了冬,她心疼心上人又有什么不对?”
“那也得考虑考虑我的处境。”
司徒策不由得叹了口气,“我也不明白了,师父与徐敬光是老冤家了,怎得儿女这么情深意笃?”
“这种事怎么说得清呢?”
傅清初笑了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司徒策笑了笑,“是啊,我还得想办法成全他们呢。”
闻言,傅清初也不禁失笑,“那是日后的事了,今晚就好好休息吧,明日我去劝她。”
司徒策叹了口气,也只能说好,“辛苦你了。”
傅清初笑了笑,“不辛苦。”
……
登基大典前三日,前尚书令崔起、辅国大将军兼云中都护卢定岳进京奔丧。
司徒策于宣和殿接见两位舅舅,再一同前往崇明殿吊唁。
二位国舅爷于先帝灵前哭得肝肠寸断,闻者生悲,又惹得司徒策悲从中来,眼泪纵横。
内侍忙将二位老国舅爷扶起来,“将军、尚书令,二位莫要再惹得陛下伤心,应宽慰陛下以玉体为重。”
二位国舅爷方才止住哭声,喊着陛下节哀,不宜悲恸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