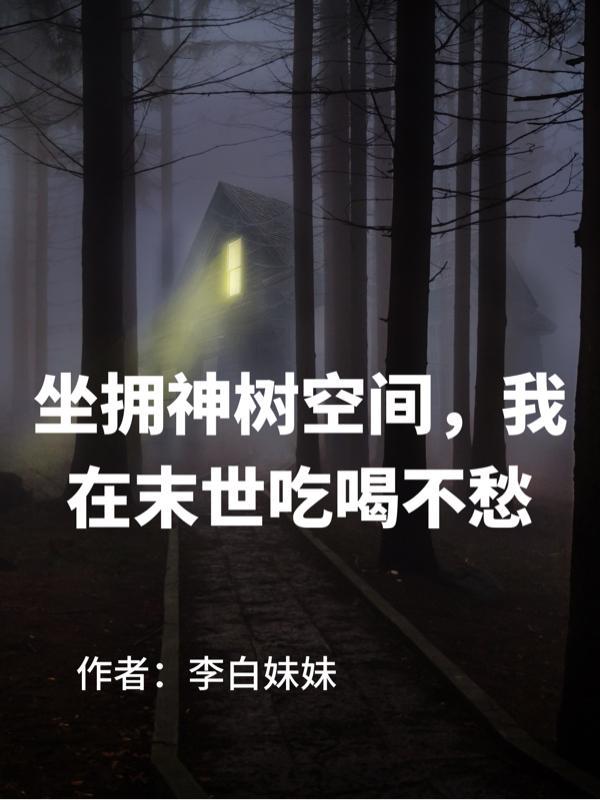爱上中文>素裹银装和银装素裹的区别 > 第五章(第5页)
第五章(第5页)
皮箱子撞在石板地上撒了架子,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中年男人慌忙俯身从地上向箱子里捡拾东西。士臻从车上跳下来,走过去弯腰看到散落一地亮晶晶的东西,恍惚在什么图册中看到过,就奇怪地问:“这位先生,你这是啥玩意儿呀,不会是电子管吧。”
“啊?哦,哦。”
中年男人一边低着头胡乱向箱子里划拉散落的小珠子、小管子,一边含混地支应着。
士臻蹲下身子准备帮着捡,男人赶紧制止住:“不用不用。”
刚一划拉完,男人没顾上关上箱子上的锁,搂起箱子就要走。
“哎——。”
大坎儿蹭地从车上跳下来拦在中年男人面前:“伙计,这么走可就不地道了吧。”
中年男人一楞,看见滚落一地有一半多已经破碎的酱坛子,马上明白过来,连忙放下皮箱朝着大坎儿拱起手深鞠一躬,说道:“哎哟,怪我急中出错疏忽了。谢谢义士,谢谢义士出手相救,谢谢啦。”
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又从长衫里摸索着掏出一摞银元递到大坎儿面前说:“不成敬意,不知能不能补偿您的损失。”
大坎儿接过银元眼光一亮,在手里颠了颠,整整六块簇新的大洋,“哟嗬,出手够大方的。得啦,这些破坛子值不了这么多的钱。”
说着,大坎儿又将银元给中年男人递了回去。
男人后退一步深鞠一躬说:“敝人初到贵地,能结识义士是在下的荣幸,请给在下一个谢恩的机会吧。”
士臻听出中年男人一口东北音儿,就跟上了一句说:“听口音这位仁兄是东北来的吧。”
“嗯哪,刚从吉林来。”
“吉林?!”
大坎儿一听乐了,大声问:“吉林哪嘎达?”
“通化。”
男人放低了声音说。
“通化,那嘎达当年我常走,好地界儿啊。还是老家来的兄弟,中啦,这钱更不能收啦。”
大坎儿再次把钱塞给男人,男人一手护着箱子一手推搡起来。
士臻赶紧上前打起圆场说:“两位都别争了。这位仁兄,就是十车的酱坛子也不值两块大洋,估摸着您这机器匣子也摔散了,这么着吧,留下两块儿,一块儿算是赔阁上宋老板的坛子钱,一块儿就当给吴大哥的酒钱吧。”
“我看中,就听我弟弟的。”
大坎儿留下两块儿大洋,将另四块塞到男人手上。
“好吧!”
男人没再坚持,收起大洋又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名片,半鞠着躬递给士臻:“在下李源吉,要在滦州车站留住一段时间,以后还请您二位多多关照。”
士臻双手接过名片,看了一眼,只见名片上工整地竖排写着:滦州火车站李源吉工程师
士臻赶忙双手深施一礼说:“原来是李大人,失敬失敬。”
接着,他又疑惑地问:“您提着行李这是要?”
“哦”
李源吉回过礼后说:“我准备去城里看望朋友,没想到小偷把我当乘客了,滦州的小偷够野蛮的,上来就硬抢呀。”
然后马上转换话题问:“敢问先生是?”
士臻再施过一礼后说:“在下不才,虞士臻,城里的塾师。”
“中啦,别才不才的啦。”
大坎儿乐着冲李源吉摆摆手:“老家兄弟,我是咱车站边的通达货栈的吴大坎儿,有啥事说句话。你要是进城的话就上车吧,顺道。”
“不了,后会有期!”
李源吉向大坎儿鞠了个躬就搂起箱子匆匆钻出围观的人群。大坎儿让石头把摔坏的坛子碎片往路边扒拉扒拉,没摔坏的四五个坛子搬上车摆放好,招呼搂着荣儿的翠儿上了车,冲着围在车边的人们喊了声:“让让喽,没啥热闹啦,散了吧。”